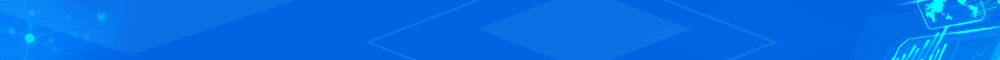閔兢 楊發(fā)祥 | “準(zhǔn)體制化”到“體制化”:制度邏輯視角下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的行動選擇
所屬地區(qū):浙江 - 杭州 發(fā)布日期:2025-06-18發(fā)布地址: 湖北
?導(dǎo) 讀?
從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制的萌芽到鄉(xiāng)鎮(zhèn)社工站的全面覆蓋,中國社會工作始終在制度邏輯的牽引下尋找與社會治理的融合路徑。進入“體制化”時代的“大社會工作”,其行動邏輯需從工具主義邏輯轉(zhuǎn)向恰當(dāng)性邏輯,在角色定位、服務(wù)取向與治理模式等方面進行全方位轉(zhuǎn)型,這既是專業(yè)自我革新的時代要求,也是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重要制度實踐。
“準(zhǔn)體制化”到“體制化”:
制度邏輯視角下
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的行動選擇
作者:閔兢 楊發(fā)祥
?摘 要?
從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制的確立到社工站的建設(shè),社會工作一直是作為能夠提供專業(yè)服務(wù)的“社會力量”被納入“準(zhǔn)體制化”的社會治理體系之中。基于制度邏輯視角,社會工作在“準(zhǔn)體制化”階段雖然被制度隱形的“合法性壓力”所約束,從而表現(xiàn)出行政趨同的行動取向,但也在工具主義邏輯的驅(qū)使下充分?jǐn)X取了制度的“可獲取性”和“可利用性”,借用政府的符號身份、行政資源和監(jiān)管評估,實現(xiàn)內(nèi)源性的借力發(fā)展。中央社會工作部的成立標(biāo)志著社會工作正式進入國家黨政體制,“體制化”語境中的社會工作需要秉持“恰當(dāng)性邏輯”,承擔(dān)起統(tǒng)合性治理的主導(dǎo)任務(wù),從角色定位、服務(wù)取向和治理模式層面進行適應(yīng)性轉(zhuǎn)型。
?關(guān)鍵詞?:準(zhǔn)體制化 制度邏輯 社會工作 社會治理
問題的緣起
?《關(guān)于構(gòu)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建設(shè)一支宏大的社會工作隊伍”,這是社會工作首次以國家話語的權(quán)威身份進入公眾視野,并由此啟動了自上而下的發(fā)展通道。從這一制度背景不難看出,發(fā)展社會工作的出發(fā)點是基于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需要,社會工作與社會治理具有天然的聯(lián)結(jié),社會工作的發(fā)展是與國家治理目標(biāo)和宏大敘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具有宏觀意義上的政治意涵[1]。
然而,制度支持的“春天”并不能天然地帶來社會工作的“春暖花開”,政府原有治理結(jié)構(gòu)與模式的路徑依賴疊加社會工作自身內(nèi)源性發(fā)展的薄弱使得作為新生力量的社會工作被“分類控制”[2]或“行政吸納”[3],從而呈現(xiàn)出以“外部服務(wù)行政化、內(nèi)部治理官僚化和專業(yè)建制化”為特征的專業(yè)異化[4]、“理論脫離實踐、實踐難以反哺理論”的循環(huán)陷阱[5]和“漂浮于既有社會體制系統(tǒng),脫嵌于既有職業(yè)分工體系、懸空于既有社區(qū)治理場域、錯位于既有社會需求結(jié)構(gòu)”的懸浮式發(fā)展[6]。這一系列批評的聲音不僅讓人產(chǎn)生疑問:中國社會工作發(fā)展的真實全貌究竟為何?利好的社會形勢與制度為社會工作帶來的只是“有增長無發(fā)展”的陷阱嗎?社會工作只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工具人”嗎?新的制度體系下中國社會工作的未來將走向何方?為了解答這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從對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流變?nèi)胧郑诖嘶A(chǔ)上透視社會工作的行動邏輯,從而為社會工作未來的理性發(fā)展提供學(xué)理依據(jù)與實踐啟發(fā)。
二理論基礎(chǔ)與分析框架?
(一)理論基礎(chǔ):傳統(tǒng)制度理論與制度邏輯視角之辨
在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一直存在著一項爭議不休的二律背反,即一方強調(diào)社會結(jié)構(gòu)與制度對個體或組織行動的束縛與制約[7],另一方則關(guān)注個體或組織對社會結(jié)構(gòu)與制度的創(chuàng)造與改造[8]。大體上,傳統(tǒng)制度理論是站在了結(jié)構(gòu)決定論一方,提出了宏觀結(jié)構(gòu)與文化如何塑造組織的一系列洞見,但是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在對個體或組織作為主體的能動性解釋上還比較薄弱。20世紀(jì)90年代初,制度邏輯視角應(yīng)運而生。經(jīng)過數(shù)年的發(fā)展,制度邏輯已成為社會學(xué)與組織理論中的核心視角[9],用于分析制度、組織與個體在社會系統(tǒng)中的相互關(guān)系。該視角對傳統(tǒng)制度理論和理性選擇理論均進行了批判,認(rèn)為前者未能將“行動者”元素置入制度語境,后者則未洞察理性的意義將根據(jù)制度秩序而變化。
基于此,制度邏輯視角將個體與組織作為“能動的行動者”置入制度語境之中,研究個體與組織是如何被制度邏輯所影響,又是如何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揮能動性甚至改造制度邏輯的。這一視角的核心假定認(rèn)為,個體與組織的利益、身份與價值觀等都嵌于現(xiàn)行的制度體系之中,行動者在受制于制度結(jié)構(gòu)的同時也能夠?qū)ι鐣a(chǎn)生自身的能動性影響,這種能動性具體體現(xiàn)在運用規(guī)則、社會關(guān)系或資源分配的能力。由此可見,制度邏輯視角作為一種雙向分析范式,有助于我們更加科學(xué)地認(rèn)識制度與行動之間的互構(gòu)性關(guān)系。
(二)分析框架:制度邏輯視角下的“制度-行動”分析
回溯中國社會工作重建后的發(fā)展歷程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工作是在強有力的制度驅(qū)動與賦能之下,才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中實現(xiàn)了快速的發(fā)展,形成了與西方社會工作發(fā)展完全不同的自上而下的演化進路。然而,高度制度化的環(huán)境在產(chǎn)生強大驅(qū)動力的同時,也會形成隱形的“合法性壓力”,使得嵌入其中的組織行為日益趨同[10],難以實現(xiàn)自主性發(fā)展。也正是這一“嵌入式”發(fā)展路徑,決定了社會工作要在給予其生長空間與發(fā)展動能的制度環(huán)境中生存,必須秉持適恰的行動理性,不斷內(nèi)化制度的各種要求并調(diào)適自身行動,才能實現(xiàn)自身的合法化生存。
同時,中國社會工作也充分辨識并擷取了制度邏輯的“可獲取性”(availability)和“可利用性”(accessibility),展現(xiàn)出在不同秩序中縱向?qū)I(yè)化的能力及其在不同制度結(jié)構(gòu)中將專業(yè)元素橫向普遍化的能力[11]。前者表現(xiàn)在社會工作一直在專業(yè)主義邏輯下,致力于為不同群體的服務(wù)對象提供專業(yè)化和個性化的服務(wù),后者表現(xiàn)在盡管不同的制度結(jié)構(gòu)確立了不同服務(wù)載體,社會工作都能夠?qū)⑵鋵I(yè)理念滲入其中、專業(yè)方法運用其中,實現(xiàn)專業(yè)服務(wù)與社會治理的嵌入和融合。也就是說,制度結(jié)構(gòu)中的社會工作并非全然的“工具人”,其在決策過程中也展現(xiàn)出運用制度的部分自治性(partial autonomy)[12]。基于此,本研究探索建構(gòu)“制度-行動”分析框架,嘗試分析在不同的制度語境下,中國社會工作的策略性行動及其背后的選擇邏輯。
三
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的“準(zhǔn)體制化”進程
?隨著我國社會結(jié)構(gòu)從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zhuǎn)型,社會治理邏輯也從簡約的總體性管控轉(zhuǎn)向復(fù)雜的技術(shù)性治理[13]。僅僅依賴政府直接解決公共問題、提供公共服務(wù),已經(jīng)難以滿足日益多元化的社會需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機制”方略成為“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zhuǎn)型的制度起點。在此基礎(chǔ)上,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了“黨委領(lǐng)導(dǎo)、政府負責(zé)、社會協(xié)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社會治理”與“社會管理”最大的區(qū)別在于治理主體的多元性與治理方式的協(xié)同性,這也是在全球公共服務(wù)問題反思的背景下中國政府進行積極職能轉(zhuǎn)型的體現(xiàn)。20世紀(jì)80年代,圍繞“政府如何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務(wù)”議題,管理學(xué)界掀起了討論熱潮,新治理理論應(yīng)運而生。該理論認(rèn)為,改變政府的施政形式,不僅需要對政府的職能部門和行動范圍進行調(diào)整,更要對處理公共問題的方式和手段進行變革,尤其是要擅于運用新興的“政策工具”,即包括市場化工具、工商管理技術(shù)和社會化手段等在內(nèi)的各種達成政策目標(biāo)的手段。社會工作正是作為這樣一種“政策工具”進入了社會治理場域,成為為弱勢群體提供公共服務(wù)的社會化手段。
2012年,民政部、財政部印發(fā)《關(guān)于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wù)的指導(dǎo)意見》,提出政府利用財政資金,采取市場化、契約化方式,面向具有專業(yè)資質(zhì)的社會組織和企事業(yè)單位購買包括困難救助、矛盾調(diào)處、人文關(guān)懷、心理疏導(dǎo)、行為矯治、關(guān)系調(diào)適、資源協(xié)調(diào)、社會功能修復(fù)和促進個人與環(huán)境適應(yīng)等在內(nèi)的社會工作專業(yè)服務(wù),以有效滿足人民群眾個性化、多樣化、專業(yè)化的服務(wù)需求。這不僅標(biāo)志著中國社會工作承接政府事務(wù)合法身份的正式確立,也意味著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技術(shù)工具被納入了社會治理機制之中。而后,各地方政府圍繞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wù)的體制機制、方式方法、具體內(nèi)容等進行了一系列實踐探索,特別是公益項目招投標(biāo)機制的建立和推廣,大大促進了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的爆發(fā)式生長。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作為一種技術(shù)主體,從一種“作為方法的項目”,逐漸成為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制的承接載體。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學(xué)有效的社會治理體制,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一些地方政府在推進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中,嘗試將社區(qū)、社會工作和社區(qū)社會組織三者有效聯(lián)動,取得了較好效果,學(xué)界將這一機制概括為“三社聯(lián)動”[14]。由此,社會工作也作為“三社聯(lián)動”的重要構(gòu)成,成為承擔(dān)社會治理功能的新載體。2017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的《關(guān)于加強和完善城鄉(xiāng)社區(qū)治理的意見》正式明確提出了社區(qū)、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多元主體協(xié)同創(chuàng)新社區(qū)治理的“三社聯(lián)動”模式,建構(gòu)了“社區(qū)組織發(fā)現(xiàn)居民需求、統(tǒng)籌設(shè)計服務(wù)項目、支持社會組織承接、引導(dǎo)專業(yè)社會工作團隊參與的工作體系”[15],進一步確立了社會工作在基層治理領(lǐng)域的主體性角色,“治理”成為新時期社會工作聚焦的主要方向。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國務(wù)院關(guān)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意見》中又在“三社聯(lián)動”的基礎(chǔ)上將社區(qū)志愿者和社區(qū)公益慈善資源納入其中,明確了“以社區(qū)為平臺、以社會工作者為支撐、以社區(qū)社會組織為載體、以社區(qū)志愿者為輔助、以社區(qū)公益慈善資源為補充”的“五社聯(lián)動”模式[16]。其中,社會工作者和社區(qū)社會組織成為彌補社區(qū)治理主體專業(yè)性短板、創(chuàng)新現(xiàn)代基層治理的重要力量。2021年,民政部下發(fā)《關(guān)于加快鄉(xiāng)鎮(zhèn)(街道)社工站建設(shè)的通知》,要求統(tǒng)籌加快推進鄉(xiāng)鎮(zhèn)街道社工站建設(shè)進度,各地政府積極響應(yīng)政策,通過政府購買街道社會工作服務(wù)站項目逐步實現(xiàn)了社工站的全面覆蓋。該通知明確提出“要發(fā)揮專業(yè)優(yōu)勢,突出社會工作特色專長,避免單純承擔(dān)事務(wù)性工作”,?這也充分體現(xiàn)了對社會工作融入基層治理的“專業(yè)服務(wù)者”的角色定位。
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抓手,社會工作在體制上的嬗變也是國家社會治理機制變革的映射。從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制的確立,到“三社聯(lián)動”與“五社聯(lián)動”治理行動框架的搭建,再到社工站的建設(shè)的過程中,社會工作雖然沒有真正地走入國家體制,卻一直是作為能夠提供專業(yè)服務(wù)的“社會力量”被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之中的。因此,筆者將這一階段稱之為社會工作的“準(zhǔn)體制化”發(fā)展階段。
借力式發(fā)展:“準(zhǔn)體制化”背景下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的行動策略
?在“準(zhǔn)體制化”階段,社會工作的主要功能是依托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社區(qū)社會組織、社工站等各類載體提供社會服務(wù),其對于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創(chuàng)新基層治理方式的核心價值也在于提供專業(yè)服務(wù),因此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的這一型態(tài)被眾多學(xué)者歸納為“服務(wù)型治理”[17]。社會工作服務(wù)型治理,是基于以人為本的治理理念,以提供專業(yè)服務(wù)為主要手段,逐漸進入基層政府讓渡的權(quán)利、資源空間中,在進行專業(yè)服務(wù)時充分考慮基層治理實踐要求,以問題導(dǎo)向、本土關(guān)懷為出發(fā)點而展開的社會服務(wù)[18]。在這一治理模式下,社會工作也在不斷調(diào)整自身的行動策略,從提供純粹的專業(yè)服務(wù)轉(zhuǎn)向治理與服務(wù)雙線并行,且在融入基層治理的具體行動中呈現(xiàn)出“借力式發(fā)展”的實踐樣態(tài)。其具體表現(xiàn)為:
(一)借名增權(quán):借行政之名奠定治理合法性基礎(chǔ)
雖然頂層設(shè)計層面的制度賦予了社會工作“合法化”的身份,但是作為需要直接面向基層群眾的服務(wù)主體,必須取得來自社會認(rèn)可的“合法性”才能真正“入場”。合法化與合法性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內(nèi)涵上卻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馬克斯·韋伯認(rèn)為,合法化是指通過法律和規(guī)則來確立權(quán)威的基礎(chǔ),而合法性則是指人們對于這種權(quán)威的自愿服從,它基于人們對于權(quán)威的認(rèn)同和信任。合法化是合法性的基礎(chǔ),但合法性才是權(quán)威能夠持續(xù)存在的關(guān)鍵[19]。
在社會知曉度和認(rèn)可度都有限的背景下,社會工作往往面臨著合法性和權(quán)威性不足的現(xiàn)實困境。為了能夠盡快獲得大眾的接受與信任,社會工作常常借用“行政之名”,以增強自身的權(quán)威性。由于各級政府是購買社會工作服務(wù)的主體,而具體的組織實施則由各級民政部門具體負責(zé)。因此,在開展社區(qū)服務(wù)時,社會工作者常常宣稱是在開展民政局的某個項目;在社區(qū)開展活動時,社會工作者常常以“行政助手”的身份積極協(xié)助,并借機尋找潛在服務(wù)對象,完成自身項目任務(wù);社會工作者會主動幫助社區(qū)分擔(dān)宣傳走訪、事務(wù)辦理、數(shù)據(jù)整理等日常工作,并借此了解社區(qū)情況、評估社區(qū)需求;社工站竭力維持與鎮(zhèn)街政府部門的緊密聯(lián)系,甚至部分社工站負責(zé)人已被納入基層黨政聯(lián)席會議,共同參與基層治理決策活動……諸如此類的嵌入實踐表明,社會工作通過“借名增權(quán)”的策略,實現(xiàn)了身份的重新“包裝”,從而大大降低了入場成本,奠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基礎(chǔ)。
(二)借資增效:借行政資源提高專業(yè)服務(wù)效能
資源獲取能力是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的生存之基,只有具備充足的資源,才能實現(xiàn)組織的使命、提升治理的效能。而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自身擁有或能夠創(chuàng)造的資源極為有限,尤其是在起步階段,來自政府購買服務(wù)的資源支持幾乎成為大部分機構(gòu)生存與發(fā)展的唯一來源。因此,借用行政資源來提高自身服務(wù)的效能成為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必要且必須的選擇。
首先,政府公共財政是各項公共政策得以實施的重要資源支撐體系,政府購買服務(wù)的資金是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開展服務(wù)的主要經(jīng)費來源。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常常通過“保持常態(tài)化聯(lián)系”“口頭溝通”與“寫好方案”等多重手段爭取更多的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以獲得專業(yè)服務(wù)和組織運營的資金保障。其次,由于政府部門購買的項目大多是為相關(guān)政策服務(wù)的,因此,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不僅會及時學(xué)習(xí)、了解國家與地方各項政策制度,而且還會敏銳地把握政策契機,有意識地將自己能供給的服務(wù)與政府部門的政策落實需求進行巧妙對接,溝通重點從“我有什么訴求”轉(zhuǎn)向“我有什么價值”,往往更容易獲得政府的青睞。最后,在開展具體服務(wù)時,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不僅常常借用政府、學(xué)校、企業(yè)、社區(qū)的場地、設(shè)備資源,調(diào)用社區(qū)的志愿者力量推進服務(wù)項目的順利開展,而且會利用政府或社區(qū)已經(jīng)搭建好的線上平臺為機構(gòu)及其項目發(fā)布信息,擴大宣傳。鏈接一切能鏈接的資源,團結(jié)一切可團結(jié)的力量,成為大多數(shù)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的“生存之道”。
(三)借機增能:借政府監(jiān)管評估實現(xiàn)自我增能
社會工作致力于改善弱勢群體的社會功能,只有高度的專業(yè)性和社會性才能保證其高質(zhì)量的服務(wù)輸出[20]。由于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創(chuàng)辦門檻相對較低、短時間內(nèi)增長速度過快,很多機構(gòu)在項目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wù)管理等方面仍處于高度依賴機構(gòu)領(lǐng)導(dǎo)者個人能力的“家庭作坊”模式,社工隊伍素質(zhì)參差不齊、隊伍整體專業(yè)能力較低等自身能力短板問題同樣突出,迫切需要自我增能。在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的運營過程中,為了保證項目成效,作為購買方的政府會通過各種方式對承接機構(gòu)進行監(jiān)管和評估。《關(guān)于加快鄉(xiāng)鎮(zhèn)(街道)社工站建設(shè)的通知》明確要求“統(tǒng)籌組建專業(yè)督導(dǎo)團隊,通過定期持續(xù)的監(jiān)督和指導(dǎo),協(xié)助開展社工站建設(shè)管理、督導(dǎo)評估和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培訓(xùn)等工作”。
專業(yè)督導(dǎo)團隊尤其是第三方評估的引入,使得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在面臨專業(yè)評價壓力的同時,也獲得了提升自身能力的契機。首先,第三方實施評估的指標(biāo)體系不僅包括場地、人員、設(shè)備等硬件條件,也涵蓋了內(nèi)部治理、服務(wù)方法、服務(wù)效能、社會評價等內(nèi)涵指標(biāo),通過多元指標(biāo)的對照考核,不僅有助于第三方對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進行全面精準(zhǔn)的評估,而且也有助于機構(gòu)對標(biāo)找差,發(fā)現(xiàn)自身在專業(yè)性和規(guī)范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從而進行針對性的改進和完善。其次,有些第三方還會對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進行實地考察和現(xiàn)場督導(dǎo),對其建設(shè)情況和專業(yè)服務(wù)開展情況給予面對面的直接指導(dǎo),這對于機構(gòu)管理體系的優(yōu)化和服務(wù)能力的提升都大有裨益。由此可見,第三方評估盡管是服務(wù)購買方實施的項目監(jiān)管手段,但對于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來說無疑也是賦權(quán)增能的有利機遇。
五
適應(yīng)性轉(zhuǎn)型:“體制化”背景下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的邏輯轉(zhuǎn)換
?在“準(zhǔn)體制化”階段,社會工作作為能動的行動主體,在嵌入制度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制度勢能,借用政府的符號身份、行政資源和監(jiān)管評估,推動了自身的內(nèi)源性發(fā)展,也為社會工作與社會治理更高層次的融合奠定了基礎(chǔ)。2023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黨和國家機構(gòu)改革方案》,作出了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的戰(zhàn)略部署,在社會工作界引起了極大討論。長期以來,中共各級組織部門對社會工作是一種“虛線管理”[21],主要負責(zé)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shè)的“牽頭抓總”,即宏觀意義上的“黨管人才”。而實施“實線管理”的則是各級民政部門,具體表現(xiàn)在民政系統(tǒng)負責(zé)社會服務(wù)的政府采購工作。而中央社會工作部和地方社會工作部的設(shè)置,將“指導(dǎo)城鄉(xiāng)社區(qū)治理體系和能力建設(shè)”“擬定社會工作政策”和“指導(dǎo)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shè)”等三項具體職責(zé)劃入其中,意味著對社會工作的黨政管理格局從“虛”到“實”的實踐轉(zhuǎn)向。在這一制度調(diào)整的背景下,社會工作也需要因應(yīng)地進行適應(yīng)性轉(zhuǎn)型,開展更多元化的自治性實踐。
(一)角色定位:從“專業(yè)社會工作”轉(zhuǎn)向“大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最初是作為一種“專業(yè)”引入國內(nèi)的,它強調(diào)的是其專業(yè)價值觀、專業(yè)理念、專業(yè)助人方法和技巧。在準(zhǔn)體制化的背景下,社會工作也正是因為具備了傳統(tǒng)行政工作所欠缺的專業(yè)性才在社會治理體系中贏得了一席之地,成為一支輔助性社會力量。隨著黨的社會工作系統(tǒng)的建立,社會工作的外延和內(nèi)涵需突破專業(yè)主義的邊界,從狹義的“專業(yè)社會工作”轉(zhuǎn)向?qū)捒趶降摹按笊鐣ぷ鳌薄?/span>
中央社會工作部是中國共產(chǎn)黨統(tǒng)領(lǐng)社會力量、解決社會領(lǐng)域的問題、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建設(shè)的工作部門[22]。這里所說的“社會工作”包含了人民信訪、基層民主、基層政權(quán)建設(shè)、人民矛盾調(diào)節(jié)、新社會組織管理與服務(wù)、志愿服務(wù)統(tǒng)籌管理等綜合治理業(yè)務(wù)。在中央社會工作部網(wǎng)站上所公布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社會工作部”的英文名稱為Society Work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工作”被翻譯為“Society Work”而非往常使用的“Social Work”,也彰顯了其更為側(cè)重社會整體的“大社會工作”的角色定位。因此,作為社會工作主體,也需要在新制度邏輯中突破社會工作的“技術(shù)化”或“臨床化”傾向和傳統(tǒng)社會工作中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qū)工作三大方法的局限,從聚焦微觀轉(zhuǎn)向宏觀微觀雙重聚焦,直面社會轉(zhuǎn)型的結(jié)構(gòu)性議題,尋求社會的體制性和整體性變革與發(fā)展,運用社區(qū)發(fā)展、組織建設(shè)、政策倡導(dǎo)和價值引領(lǐng)等干預(yù)策略實現(xiàn)“建構(gòu)有力的社會”的宏觀目標(biāo)[23]。
(二)服務(wù)取向:從“以困弱群體為中心”轉(zhuǎn)向“以人民為中心”
長期以來,社會工作面向的服務(wù)對象主要是在身體狀況、精神狀態(tài)、家庭能力、社會資本等方面處于弱勢地位的“困弱群體”。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工作以協(xié)同者的身份較廣泛地參與到了基層社會治理之中,從協(xié)助解決社區(qū)中的社會矛盾,到催化居民提升社區(qū)共識,再到協(xié)助黨建引領(lǐng)下的各種居民活動,促進提升了社會治理效能[24]。社會的快速轉(zhuǎn)型與發(fā)展使得當(dāng)前我國的社會治理環(huán)境也發(fā)生了劇烈的改變,利益格局的重新建構(gòu)與社會關(guān)系的巨大解構(gòu)同時并存,人民需求的多元性與多層次性日益凸顯,各種新社會組織、行業(yè)協(xié)會、非公經(jīng)濟、志愿者組織等紛紛涌現(xiàn),上層建筑也要適應(yīng)新的形勢主動變革。
中央社會工作部負責(zé)統(tǒng)籌指導(dǎo)人民信訪工作,指導(dǎo)人民建議征集工作,統(tǒng)籌推進黨建引領(lǐng)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quán)建設(shè),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全國性行業(yè)協(xié)會商會黨的工作,協(xié)調(diào)推動行業(yè)協(xié)會商會深化改革和轉(zhuǎn)型發(fā)展,指導(dǎo)混合所有制企業(yè)、非公有制企業(yè)和新經(jīng)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yè)群體黨建工作等。這不僅意味著社會工作從“協(xié)同者”變成了“主導(dǎo)者”,而且要求社會工作要以更高的戰(zhàn)略思維和統(tǒng)籌能力,適應(yīng)新時代發(fā)展需求,拓寬服務(wù)對象范疇,更好地回應(yīng)各類群體多層次、差異化和個性化的新需求。“Society Work”代表了一個更加全面的社會服務(wù)體系,不僅僅是針對困弱群體的具體服務(wù),而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以人民為中心”,著眼于整個社會建設(shè)與發(fā)展的治理體系。
(三)治理模式:從“服務(wù)型治理”轉(zhuǎn)向“統(tǒng)合性治理”
在機構(gòu)改革之前,社會工作的相關(guān)職能分散在組織部門、宣傳部門、民政部門等多個黨政部門中,缺乏集中的領(lǐng)導(dǎo)和力量的整合,因而對于社會治理的推動作用也較為有限。社會工作要承擔(dān)系統(tǒng)化的社會治理職責(zé),必須跳出“服務(wù)型治理”的單一型態(tài),在介入領(lǐng)域和介入層次上同時做“增量拓展”和“深度浸潤”,以“統(tǒng)合性治理”的格局對各類社會治理主體進行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實現(xiàn)治理體系的現(xiàn)代化。這里的“統(tǒng)合”至少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治理主體的整合,二是治理職責(zé)的集中。中央社會工作部的組建正在通過機構(gòu)的整合實現(xiàn)職責(zé)的集中,即由社會工作部統(tǒng)籌牽總民政、工青婦等各相關(guān)部門,全面整合政府和社會資源,統(tǒng)籌實施包括信訪、基層政權(quán)建設(shè)、基層民主、社區(qū)治理、弱勢群體幫扶等在內(nèi)的行政管理與公共服務(wù)輸出[25],全面實現(xiàn)黨在社會領(lǐng)域的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
一直以來,很多學(xué)者認(rèn)為社會工作要在中國本土化實踐中獲得一席之地,必須保持并不斷加強專業(yè)的獨立性。實際上,“大社會工作”與“專業(yè)社會工作”之間并非彼此互斥的零和博弈關(guān)系,而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濟的共生關(guān)系。連接本土實踐情景與滿足基層治理現(xiàn)代化的訴求才是社會工作賴以生存的最大現(xiàn)實[26],如果固守專業(yè)獨立性的唯一堅持而缺乏對現(xiàn)實問題的回應(yīng)和對實踐的指導(dǎo)作用,只會使得自身的角色更為邊緣化。在體制化的新發(fā)展階段,社會工作應(yīng)擔(dān)負起政策宣導(dǎo)、組織建設(shè)、價值引領(lǐng)、文化培育等宏觀使命,在立足專業(yè)服務(wù)的基礎(chǔ)上聚焦社會建設(shè),以更為“彌散”的形態(tài)融入基層治理和國家治理大局之中。
六
工具主義邏輯與恰當(dāng)性邏輯:制度秩序情境變遷下的理性轉(zhuǎn)變
?制度邏輯視角的獨特性在于它在社會結(jié)構(gòu)的語境下觀察行動,并同時注重研究行動主體的能動性。如何解釋結(jié)構(gòu)與能動性之間的關(guān)系是制度邏輯視角下最重要的元理論難題,其關(guān)鍵就在于理解作為行動者的個體或組織如何在受制于制度的情境下作出理性的行動選擇[27]。迄今為止,傳統(tǒng)的制度理論對這一問題仍無法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們對“理性”這一概念采用了二分法定義,即將理性決策對立于非理性決策,這種非此即彼的界定自然無法解讀復(fù)雜并處于不斷變化之中的主體行動。而制度邏輯視角認(rèn)為,理性的意義是隨著制度秩序情境的變化而變化的,主體行動的決策并非完全理性也非完全非理性,而是一個高度情境化的選擇。基于此,制度邏輯視角提出了兩種理性的變體:工具主義邏輯和恰當(dāng)性邏輯[28]。工具主義邏輯回答的是“在這種制度結(jié)構(gòu)中我采取什么行動才能獲得最大利益”;而恰當(dāng)性邏輯則回答的是“這樣的制度環(huán)境對我的期望是什么,我怎么做才能滿足這些期望”。
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的制度經(jīng)過了從“準(zhǔn)體制化”到“體制化”的演變,社會工作的行動邏輯與理性基礎(chǔ)也在依據(jù)制度的變遷發(fā)生著改變。隨著社會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單位制逐漸消解,社區(qū)制逐步確立,這對于治理結(jié)構(gòu)的重塑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在建設(shè)“服務(wù)型政府”的理念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發(fā)揮政府主導(dǎo)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以及“激發(fā)社會組織活力,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wù)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dān)”等創(chuàng)新舉措推動了國家治理權(quán)限進一步向社會主體釋放,客觀上為社會工作承接治理職能讓渡了權(quán)力和空間。然而,在機構(gòu)改革之前,尚處于“準(zhǔn)體制化”階段的社會工作的實踐樣態(tài)主要表現(xiàn)為由民政部門以政府購買服務(wù)的方式,以社會工作服務(wù)機構(gòu)、社工站等為載體,在社會救助、困弱群體幫扶等特定領(lǐng)域提供專業(yè)社會工作服務(wù),扮演的是外在于政府的、發(fā)揮協(xié)同作用的“社會力量”的角色。基于對制度的承認(rèn)與制度的約束同時并存的形勢研判,社會工作選擇了工具主義邏輯,一方面在“軸心-外圍”的治理結(jié)構(gòu)中,以政策工具的身份助力基層治理與社會建設(shè),從而鞏固自身的合法性身份;另一方面,也依托國家與社會同構(gòu)的建設(shè)范式,借助制度勢能,健全自身組織結(jié)構(gòu),增強自身能力,在有限的制度框架中進行利益調(diào)適和行動決策,從而謀求政府的注意力分配與自身的內(nèi)源性發(fā)展。
《黨和國家機構(gòu)改革方案》對于中央社會工作部的職能界定釋放了一個核心信號,即對于“社會工作”的全新界定超越了學(xué)術(shù)界“專業(yè)社會工作”和實務(wù)界“專業(yè)社會工作服務(wù)”的傳統(tǒng)認(rèn)識,是包含“專業(yè)社會工作”在內(nèi)的寬口徑的“大社會工作”。從中央到地方社會工作部的組建將社會工作從從屬角色引向基層治理的主舞臺,成為獨當(dāng)一面的基層治理主角。其實質(zhì)是從黨管社會工作人才的“虛線管理”向黨管社會工作的“實線管理”的轉(zhuǎn)化,意味著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新階段,社會工作以“體制化”的身份承擔(dān)包括人民信訪,人民意見征集,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quán)建設(shè),行業(yè)協(xié)會商會管理,混合所有制企業(yè)、非公有制企業(yè)和新經(jīng)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yè)群體黨建,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shè)等六項主要職能[29],這標(biāo)志著黨以“社會工作”之名統(tǒng)籌推進基層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建設(shè)。在此背景下,社會工作必須回答和反思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樣的制度環(huán)境對我的期望是什么,我怎么做才能滿足這些期望”,這也意味著其行動理性從工具主義邏輯向恰當(dāng)性邏輯的轉(zhuǎn)換。這種轉(zhuǎn)換對社會工作來說是一大進步,因為它不僅考慮自身行動會帶來的主體利益,還考慮到自身行動對社會的義務(wù)和貢獻。恰當(dāng)性邏輯驅(qū)動下的“大社會工作”也需要以更大的格局和擔(dān)當(dāng)承擔(dān)起統(tǒng)合性治理的總導(dǎo)演,擴展自己的歷史使命,從福利服務(wù)的提供者轉(zhuǎn)型為承擔(dān)福利服務(wù)與社會治理的復(fù)合角色[30],回應(yīng)黨和國家對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的“硬核需求”。
七
結(jié)論與討論
?制度邏輯視角認(rèn)為制度是具有歷史權(quán)變性的,是隨著歷史的演化而變化的。從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制的確立,到“三社聯(lián)動”與“五社聯(lián)動”治理行動框架的搭建,再到社工站的建設(shè),社會工作一直是作為能夠提供專業(yè)服務(wù)的“社會力量”被納入“準(zhǔn)體制化”的社會治理體系之中。在這一階段社會工作雖然被制度隱形的“合法性壓力”所約束,從而表現(xiàn)出行政趨同的行動取向,但也在工具主義邏輯的驅(qū)使下充分?jǐn)X取了制度的“可獲取性”和“可利用性”,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性行動,通過借用政府的符號身份、行政資源和監(jiān)管評估,實現(xiàn)內(nèi)源性的借力發(fā)展。中央社會工作部的成立標(biāo)志著社會工作正式進入國家黨政體制,“體制化”語境中的社會工作需要秉持“恰當(dāng)性邏輯”,承擔(dān)起統(tǒng)合性治理的主導(dǎo)任務(wù),從角色定位、服務(wù)取向和治理模式層面進行適應(yīng)性轉(zhuǎn)型。
基于對社會工作融入社會治理整體生命歷程的爬梳,可以發(fā)現(xiàn)社會工作的行動邏輯統(tǒng)一于社會發(fā)展不同階段下國家與社會關(guān)系的調(diào)構(gòu)與黨政發(fā)展戰(zhàn)略的調(diào)整,是制度演進與自身發(fā)展互構(gòu)作用的產(chǎn)物,是自上而下的治理需求與自下而上的主體供給相互嵌合的結(jié)果。實踐與身份從根本上與制度邏輯相互關(guān)聯(lián),并且可以通過它們與特定實證環(huán)境中的制度邏輯的關(guān)系來有效地理解它們的具體行為[31]。從社會工作借行政之名開展服務(wù)型治理,到黨借社會工作之名開展統(tǒng)合性治理,也體現(xiàn)了制度邏輯視角下行動者在受制于制度的同時也在形塑著新的制度這一雙向建構(gòu)論斷。舊制度主義與行動的聯(lián)系更清晰,新制度主義與結(jié)構(gòu)的聯(lián)系更明確[32],而制度邏輯視角則結(jié)合性建構(gòu)了結(jié)構(gòu)、制度與行動之間的同構(gòu)性關(guān)系。當(dāng)然,制度的約束作用往往是十分強大的,用一種狹隘的、片面強調(diào)能動性的視角來徹底取代更具結(jié)構(gòu)主義視角的制度理論也是沒有意義的[33]。本研究引入制度邏輯視角旨在發(fā)展一種更加平衡的制度主義方法來理解制度結(jié)構(gòu)與實踐行動之間的關(guān)系,并借此澄清行動者并非完全被動的,其行動也可以是強有力的、戰(zhàn)略性的,這也是催化制度變遷的重要動力。用這一視角來展望我國社會工作的未來,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社會工作將以新的戰(zhàn)略定位切基層治理之脈、定統(tǒng)合治理之維;另一方面,社會工作不僅具有專業(yè)理性,也具有人文關(guān)懷的天然秉性,在中國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場域下,合乎人民利益的理性才是真正的價值理性,大社會工作也將突破專業(yè)理性的定勢,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性,重塑融合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國共產(chǎn)黨群眾工作優(yōu)良傳統(tǒng)與社會工作專業(yè)價值為一體的治理新生態(tài)。2024年11月,***對社會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社會工作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guān)黨長期執(zhí)政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guān)社會和諧穩(wěn)定和人民幸福安康。”這為新時代社會工作的發(fā)展舉旗定向,未來社會工作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緊扣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以改善民生福祉為核心,走向融合行政性、人民性、專業(yè)性和本土性于一體的國家社會工作[34]。
?注釋:
[1]馬鳳芝.從社會工作與社會政策關(guān)系看社會工作的政策品性——兼論社會政策在社會工作中的走向[J].河北學(xué)刊,2022(01):180-190.
[2]康曉光,韓恒.分類控制:當(dāng)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guān)系研究[J].開放時代,2008(02):30-41.
[3]康曉光,韓恒.行政吸納社會——當(dāng)前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guān)系再研究[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7(02):116-128.
[4]朱健剛,陳安娜.嵌入中的專業(yè)社會工作與街區(qū)權(quán)力關(guān)系——對一個政府購買服務(wù)項目的個案分析[J].社會學(xué)研究,2013(01):43-64+242.
[5]葛道順.社會工作轉(zhuǎn)向:結(jié)構(gòu)需求與國家策略[J].社會發(fā)展研究,2015(04):1-23+238.
[6]侯利文,徐永祥.被忽略的實踐智慧:邁向社會工作實踐研究的新方法論[J].社會科學(xué),2018
(06):82-93.
[7]Wrong, D. H.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1(26):183-193.
[8]Child, J.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The Role of Strategic Choice[J].Sociology,1972(6):1-22.
[9]Greenwood, Royston, Oliver, Christine, Sahlin-Andersson, Kerstin, and Suddaby, Roy(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M]. Thousand Oaks,CA:Sage,2008.
[10]楊寶,肖鹿俊.技術(shù)治理與制度匹配:社會工作本土化路徑“雙向趨同”現(xiàn)象研究[J].學(xué)習(xí)與實踐,2021(10):108-118.
[11][12][27][32]帕特里夏·H.桑頓,威廉·奧卡西奧,龍思博.制度邏輯:制度如何塑造人和組織[M].汪少卿,杜運周,翟慎霄,張容榕,譯,杭州: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20:20,8,22,150.
[13]渠敬東,周飛舟,應(yīng)星.從總體支配到技術(shù)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jīng)驗的社會學(xué)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9(06):104-127+207.
[14]徐永祥,曹國慧.“三社聯(lián)動”的歷史實踐與概念辨析[J].云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6(02):54-62.
[15]中共中央 國務(wù)院關(guān)于加強和完善城鄉(xiāng)社區(qū)治理的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
[16]中共中央 國務(wù)院關(guān)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意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0.
[17]王思斌.社會工作在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種基礎(chǔ)—服務(wù)型社會治理[J].社會工作,2014(01):3-10+150.
[18]王建平.服務(wù)型治理:鄉(xiāng)鎮(zhèn)社工站的實踐轉(zhuǎn)向及其意義[J].中國社會工作,2023(09):8.
[19]于柏華.韋伯論政治合法性與合法律性及其現(xiàn)實意義[J].學(xué)習(xí)與探索,2009(06):96-99.
[20]向德平,黃家文.雙向嵌入與政社關(guān)系的重構(gòu)——以T市市級社工站與政府互動為例[J].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24(08):231-240.
[21][25]孟亞男,林順利.機構(gòu)改革背景下社會工作參與基層治理的適應(yīng)性轉(zhuǎn)型[J].河北學(xué)刊,2024(05):183-191.
[22]王思斌.發(fā)展好“大社會工作”[J].中國社會工作,2023(10):6.
[23]何雪松.積極而非激進:宏觀社會工作的中國圖景[J].學(xué)海,2020(01):119-122.
[24]王思斌.發(fā)揮社會工作在社會建設(shè)中的綜合作用[N].2024-07-16(5).
[26]趙秀玲.中國基層治理研究轉(zhuǎn)向及其思考[J].東南學(xué)術(shù),2022(06):98-106+248.
[28] March, James G.,and Olsen, Johan P.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 tional Basis of Politics[M]. New York: Free Press,1989.
[29]中國政府網(wǎng).中共中央 國務(wù)院印發(fā)《黨和國家機構(gòu)改革方案》[EB/OL].[2024-03-26]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48649.htm.
[30]李迎生.擴展社會工作的傳統(tǒng)界限[J].社會工作,2023(06):9-12+98.
[31] Hirsch, Paul M., and Lounsbury, Michael .Ending the Family Quarrel: Towards a Reconciliati
-on of the “Old”and “New” Institutionalism[J].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1997(40):415.
[33]Schneiberg, Marc.What's on the Path? Path Dependence, 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and the Problem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U.S. Economy, 1900-1950[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07(5): 47-80.?
[34]衛(wèi)小將.國家社會工作的理念、內(nèi)涵與發(fā)展策略[J].山東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24(11):1-9.
(▲向下滑動查看全部注釋)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共同富裕進程中縣域鄉(xiāng)村振興研究”(項目編號:22VRC177)、江蘇省社科基金年度項目“江蘇青年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與鄉(xiāng)村振興的聯(lián)動路徑與政策支持研究”(項目編號:24SHB011)。
?作者簡介?
閔 ? 兢,淮陰工學(xué)院人文學(xué)院蘇北發(fā)展研究院副教授;
楊發(fā)祥,華東理工大學(xué)應(yīng)用社會學(xué)研究所所長、二級教授。
本文原載于《學(xué)習(xí)與實踐》2025年第5期。
-end-
01??《學(xué)習(xí)與實踐》2025年第5期目錄及摘要
02?反思性與行動流的構(gòu)建:關(guān)于社會工作者“知行彌合”的思考——基于結(jié)構(gòu)化理論的視角(作者:劉振)
03?開卷應(yīng)考到自洽調(diào)適:追趕型城市數(shù)字政府建設(shè)的解釋路徑(作者: 龔宏齡 原珂 吳秋怡)
04?黨建引領(lǐng)、數(shù)字賦能與基層網(wǎng)格化治理效能提升——基于桂東P區(qū)的調(diào)研分析(作者: 張國磊 劉俊茹)
05?從“養(yǎng)”到“育”:基層資源傳遞模式轉(zhuǎn)向——基于社區(qū)公益基金建設(shè)項目的探索(作者: 任敏 呂江蕊)
06?數(shù)智化時代社會救助的敏捷治理:基于低收入人口的動態(tài)監(jiān)測分析(作者:匡亞林 吳佳馨)
07?數(shù)字社會的文化圖景:算法推薦與民族志解讀(作者: 高進 黃種興)
# 推薦欄目??
(點擊下方標(biāo)題前往欄目閱讀)
| 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 |
| 數(shù)字社會 |
| 基層善治 |
| 政治 |
| 經(jīng)濟 |
| 法律 |
| 公共管理 |
| 社會 |
| 文化 |
| 新聞與傳播 |

![]()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查看免費推送
- 衢州招標(biāo)網(wǎng)
- 杭州招標(biāo)網(wǎng)
- 湖州招標(biāo)網(wǎng)
- 嘉興招標(biāo)網(wǎng)
- 寧波招標(biāo)網(wǎng)
- 紹興招標(biāo)網(wǎng)
- 臺州招標(biāo)網(wǎng)
- 溫州招標(biāo)網(wǎng)
- 麗水招標(biāo)網(wǎng)
- 金華招標(biāo)網(wǎng)
- 舟山招標(biāo)網(wǎng)
- 建湖縣招投標(biāo)
- 湖北|網(wǎng)上采購招標(biāo)平臺
- 高坪區(qū)財政局
- 陜西省及政府采購與招標(biāo)網(wǎng)
- 宣城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鎮(zhèn)江市丹徒區(qū)
- 廣南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政府采購招標(biāo)方式
- 廣東建設(shè)網(wǎng)
- 沙洋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秦都區(qū)人民政府
- 天津|陽光采購平臺招標(biāo)信息
- 采購洗碗機
- 溫州裝修招標(biāo)
- 海滄區(qū)人民政府
- 上海地鐵招投標(biāo)告示
- 普蘭店政府招標(biāo)網(wǎng)
- 凌源市政府采購網(wǎng)
- 上海交易采購中心
- 信息招標(biāo)網(wǎng)
- 山東省|招投標(biāo)公共信息服務(wù)平臺
- 河北張家口下花園區(qū)應(yīng)急管理局
- 昌平招標(biāo)網(wǎng)
- 建工集團招標(biāo)
- 晉城招標(biāo)工程
- 彬州市人民政府
- 臨沭縣政務(wù)服務(wù)中心
- 防暴頭盔
- 寧波招投標(biāo)余姚分中心
- 中國石油招標(biāo)平臺
- 高州市財政局
- 撫順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 新干縣財政局
- 塔河縣人民政府
- 國信招投標(biāo)信息網(wǎng)
- 湖北|省政府采購招標(biāo)平臺
- 貴州省招標(biāo)有限公司
- 高速公路招標(biāo)公告
- 白酒物流配送招標(biāo)
- 樂山市財政局
- 廣陵區(qū)人民政府
- 印刷政府采購
- 電源招標(biāo)采購網(wǎng)
- 膠州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廈門市思明區(qū)
- 充電樁工程招標(biāo)流程
- 南陽市招標(biāo)中心
- 什邡市財政局
- 江蘇公共資源
- 干部培訓(xùn)項目招標(biāo)
- 沈河區(qū)人民政府
- 郫都區(qū)人民政府
- 競爭性招標(biāo)采購5G
- 張北縣政府公開信息
- 安徽大學(xué)
- 清華大學(xué)|招標(biāo)采購中心
- 宜都市招投標(biāo)中心
- 皖西衛(wèi)生職業(yè)學(xué)院
- 周口招標(biāo)代理
- 南京仙林大學(xué)城
- 克東縣人民政府
- 哈密政府采購
- 河北省供電公司招標(biāo)公告
- 昌樂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威海市環(huán)翠區(qū)
- 國鐵采購平臺
- 濱海縣衛(wèi)生局招標(biāo)網(wǎng)
- 湖南招標(biāo)信息網(wǎng)
- 鄭州招投標(biāo)人員招聘
- 沭陽招標(biāo)采購網(wǎng)
- 海南建設(shè)交易網(wǎng)
- 寧夏建設(shè)網(wǎng)
- 鋼筋切斷機招標(biāo)采購
- 平遙縣電力交易中心
- 天津招標(biāo)投標(biāo)公共服務(wù)平臺
- 河北華電招標(biāo)網(wǎng)
- 湖北招標(biāo)與采購網(wǎng)
- 清江浦區(qū)人民政府
- 關(guān)于醫(yī)院政府采購招標(biāo)流程
- 泉州招標(biāo)代理
-
 聯(lián)系客服
聯(lián)系客服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信息發(fā)布
信息發(fā)布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招標(biāo)訂閱
招標(biāo)訂閱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商機挖掘
商機挖掘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數(shù)據(jù)定制
數(shù)據(jù)定制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標(biāo)書代寫
標(biāo)書代寫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資質(zhì)辦理
資質(zhì)辦理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投標(biāo)咨詢
投標(biāo)咨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證書查詢
證書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綠色報告查詢
綠色報告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