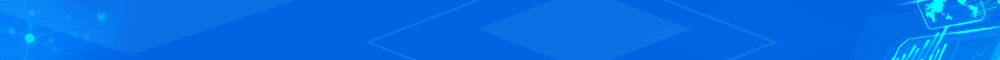張春蕾|曲牌【山坡羊】繁衍考釋
所屬地區(qū):江蘇 - 南京 發(fā)布日期:2025-06-02發(fā)布地址: 北京
曲牌【山坡羊】繁衍考釋
張春蕾
摘 ? ? 要:本文將曲牌【山坡羊】分為四種類型,梳理了每種類型的民間流變繁衍,構(gòu)建曲牌發(fā)展的古今關(guān)聯(lián)。其中昆腔【山坡羊】數(shù)量眾多,自成體系,在自身發(fā)展與流變時(shí)出現(xiàn)格律突破與個(gè)性化變異。弦索腔【山坡羊】承繼北曲類【山坡羊】七聲特征,唱腔發(fā)展較成熟,同名曲牌在變化板式、調(diào)式和生旦分腔之后,朝著板腔化、俗化的道路邁進(jìn)。俗曲類【山坡羊】在流變過程中,文辭、唱腔旋律與原始形態(tài)有所關(guān)聯(lián),但漸變漸遠(yuǎn)。器樂類【山坡羊】體現(xiàn)出流變繁衍的四個(gè)層次:完整—四句體—四句體加變化—僅保留第一句典型音調(diào)。從【山坡羊】在民間復(fù)雜多樣的流變中,我們可窺探“曲牌”的歷史繁衍進(jìn)程。關(guān)鍵詞:昆腔;高腔;俗曲;器樂曲;弦索腔中圖分類號:J607?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2-9923(2025)03-0069-11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5.03.007作者簡介:張春蕾(1989— ?),女,博士,中央音樂學(xué)院音樂學(xué)系教師,中央音樂學(xué)院專職研究員。基金信息:本文為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diǎn)研究基地重大項(xiàng)目“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傳承和創(chuàng)新機(jī)制研究”(項(xiàng)目編號:22JJD7600001)、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優(yōu)秀博士論文出版項(xiàng)目“曲牌‘山坡羊’研究”(項(xiàng)目編號:21FYB075)的階段成果。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lif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han Po Yang] Tune
○Zhang Chunlei
Abstract:?This paper categorizes the [Shan Po Yang] tune into four types, delineating the evolution and proliferation of each form within folk traditions and thereby constructing a link between it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Among these, the Kun Style [Shan Po Yang] is notably numerous and forms a self-contained system, exhibiting breakthroughs in metric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zed variations during its evolution. The String and Bow Style [Shan Po Yang] inherits the seven-to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ern Tune [Shan Po Yang] and has developed a relatively mature vocal style; after modifications in rhythmic patterns, modal structure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oles, the tune has embarked on a path toward standardized and popularized forms. The Folk Tune type [Shan Po Yang] maintains certain connections in its lyrics and melodic phrasing to its original form throughout its evolution, although it gradually diverges. The Instrumental type [Shan Po Yang] manifests four distinct levels of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a complete form; a four-line form; a four-line form with variations; and a form in which only the first line's characteristic melody is preserved. Through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evolution of [Shan Po Yang] in folk traditions, we can glimpse the historical proliferation process of the tune pattern.
Keywords:?Kun Style;Gao Style;Folk Tune;Instrumental Tune;String and Bow Style
序 ? ? 言
【山坡羊】是中國眾多曲牌中十分有代表性的1支,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而且在民間戲曲、器樂、說唱、民歌中廣泛流傳。筆者拙文《曲牌【山坡羊】歷史發(fā)展的四種類型》?1?(以下簡稱“《歷史》文”)對這一曲牌的歷史樣貌進(jìn)行了梳理與分析,將這一曲牌分為北曲、南曲、俗曲、器樂四種類型,由于篇幅有限,僅對其歷史發(fā)展情況進(jìn)行了總結(jié)歸納,本篇?jiǎng)t在四種類型基礎(chǔ)之上,聚焦這一曲牌在民間如何進(jìn)一步繁衍流變,以更加全面地呈現(xiàn)曲牌發(fā)展樣貌。此曲牌的歷史文獻(xiàn)筆者在“《歷史》文”中已略作綜述。今人有關(guān)這支曲牌的研究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較為宏觀地從曲牌整體歷史發(fā)展進(jìn)行全國范圍內(nèi)對比分析的論文和著作,一類是專門研究曲牌【山坡羊】在某一樂/劇種或某個(gè)歷史階段具有某種形態(tài)的論文。前者文獻(xiàn)較少,主要有楊棟《【山坡羊】曲調(diào)源流述考》,馮光鈺《中國曲牌考》與《中國歷代傳統(tǒng)曲牌音樂考釋(選載之七)》,板俊榮、張仲樵《中國古代民間俗曲曲牌、曲詞及曲譜考釋》,武俊達(dá)《曲牌【山坡羊】研究》與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這六篇/部論文或著作;后者則多是這一曲牌的個(gè)例研究,或在特定樂/劇種中的研究。從目前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前輩學(xué)者已關(guān)注到這一曲牌的歷史發(fā)展、音樂形態(tài)流變等問題,也在形態(tài)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對這一曲牌研究樣本較少、曲牌采集區(qū)域較為集中等問題。有關(guān)本文“南曲”“北曲”“俗曲”“器樂”四大類型在元明清的詞格、發(fā)展規(guī)模、歷史樣貌與音樂形態(tài)等,可參考“《歷史》文”,此文中不做過多贅述,僅在每部分開頭處大致概括,以求對每種類型的歷史源頭有直觀了解,從而構(gòu)建較完整的古今繁衍路徑。“《歷史》文”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為:四種類型的音樂形態(tài)具有很強(qiáng)的相似性。若說前篇的結(jié)論是“相似”,是曲牌早期樣態(tài)的穩(wěn)定與統(tǒng)一,則本篇可看出其民間千姿百態(tài)和多元復(fù)雜的發(fā)展變遷脈絡(luò)。一、?南曲類【山坡羊】在昆腔和高腔中的不同層次變化
歷史上南商調(diào)【山坡羊】興盛于明代,在明傳奇中得到廣泛應(yīng)用,每句字?jǐn)?shù)也有所增加。南曲【山坡羊】具有完整詞格,羽調(diào)式,12句或11句唱詞,五聲音階,旋律核心元素以Re Do La(低音)三音列及其移位、逆行等變化構(gòu)成旋律進(jìn)行式。全曲以眾多環(huán)繞式三音列構(gòu)成,形成細(xì)膩委婉的行腔特色。南曲類【山坡羊】主要在眾多昆曲劇目中使用,散曲形式較少。在每首傳統(tǒng)昆腔【山坡羊】中,音樂形態(tài)與詞格較穩(wěn)定。以被稱作傳奇劇目“標(biāo)準(zhǔn)格式”《琵琶記·吃糠》中的1支【山坡羊】為典型案例。(見表1)表1 昆曲《琵琶記》【山坡羊】“亂荒荒不豐稔的年歲”結(jié)構(gòu)?2?(掃描文首二維碼)南曲類【山坡羊】以昆劇唱腔為代表,句式和音樂都非常穩(wěn)定相似。筆者搜集到的百余支昆曲【山坡羊】樂譜,多數(shù)有完整的“南羊”詞格,音樂與《琵琶記·吃糠》擁有相同的行腔特色與旋律進(jìn)行方式、句式結(jié)構(gòu)與落音。但每1支也并非完全相同,會(huì)有各自的行腔特色,甚至出現(xiàn)句式、板式變化,同一首在不同版本記錄中也呈現(xiàn)具體潤腔的不同,體現(xiàn)出昆腔【山坡羊】在不同地域流傳,以及不同人演唱時(shí)表現(xiàn)出藝術(shù)化的個(gè)性處理。昆腔【山坡羊】集中于蘇、浙、滬一帶以及湘昆、北昆。除昆劇使用,其他劇種亦傳,如臺州亂彈、湘劇、贛劇、徽劇、粵劇、廣東正字戲中的昆腔等。昆腔【山坡羊】旋律形態(tài)穩(wěn)定,偶有一些地域性變化。如太湖流域的昆劇、衡陽湘劇保留了委婉的“水磨”風(fēng)格;正字戲昆腔中保留了較粗獷的“草昆”風(fēng)格;贛劇、徽劇的昆腔沿襲了原昆山腔面貌,熱烈高亢;粵劇【山坡羊】融入大量方言,音階、調(diào)式“廣味兒”濃郁。昆曲【山坡羊】在各地流傳中展現(xiàn)出格律和旋律框架一致下的有限變化,一些格律發(fā)生變化的現(xiàn)象如名劇《牡丹亭·驚夢》中,【山坡羊】從12句變?yōu)?3句,被沈璟等格律家指為“不可歌”,然而這種不守格律的“另類”做法卻顯新意,成就了杜麗娘的絕唱。這一段格律增加的同時(shí),音樂也發(fā)生了變化,在傳統(tǒng)第6句的唱腔處擴(kuò)展為2句,旋律相應(yīng)增加,然而樂句開始和結(jié)束處的旋律框架和骨干音仍保持著統(tǒng)一。目連戲高腔【山坡羊】也展現(xiàn)出與昆腔【山坡羊】相同的詞格與相似的旋律,可看作南曲類【山坡羊】的流變。目連戲有4個(gè)唱段都是《夢兒里分明見我娘》,分別在安徽目連戲,江蘇高淳陽腔,湖南祁劇、祁陽戲中。4個(gè)唱段還有一個(gè)共性,曲牌都叫【紅衲襖帶山坡羊】,從名稱可見,為集曲形式。透視這4支“目連戲羊”,可見它們與昆劇中的形態(tài)存在遠(yuǎn)近關(guān)系。下面把昆曲傳統(tǒng)唱段中《幽閨記·雙逢》中的最后1句,以及4個(gè)唱段的最后1句列出對比。(見譜例1)譜例1 昆曲《幽閨記·雙逢》和安徽目連戲、高淳陽腔、祁劇、祁陽戲的“山坡羊”結(jié)尾句?3?(掃描文首二維碼)可見安徽目連戲與祁劇的結(jié)尾句旋律框架、形態(tài)與昆曲【山坡羊】相似;高淳陽腔結(jié)尾保留了相同落音,樂句前半部分則更多是念唱風(fēng)格的同音反復(fù);安徽目連戲變化更大,旋律框架和落音都有所改變。南曲類【山坡羊】以昆曲為依托,數(shù)量眾多,自成體系,影響廣泛。在自身發(fā)展與流變時(shí)展現(xiàn)不同層次:既有曲牌自身突破格律的發(fā)展,也有流傳到各地之后發(fā)生的個(gè)性化變異,還有流變到姊妹聲腔后產(chǎn)生的旋律變化。總之,南曲類【山坡羊】在原始曲牌的詞格和旋律框架下,沒有脫離歷史上“曲牌”的概念,自身系統(tǒng)嚴(yán)謹(jǐn)規(guī)整,藝術(shù)化程度最高。二、?弦索腔【山坡羊】——北曲類【山坡羊】的民間遺存
北中呂【山坡羊】是這一曲牌的早期形式,元代南曲類【山坡羊】鮮見,北曲類【山坡羊】則大量存在,十一句體,格律標(biāo)準(zhǔn),多為文人散曲,也有少量在雜劇、南戲中使用。早期北曲類【山坡羊】目前所存樂譜很少,只能見到《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簡稱《九宮大成》)中的3支,且其中2支都入商調(diào),僅有1支入中呂宮。入商調(diào)的2支與南曲類旋律有關(guān)聯(lián),入中呂宮的1支旋律形態(tài)獨(dú)特,與其他旋律形態(tài)均不似。北曲類【山坡羊】與南曲類【山坡羊】最大的區(qū)別是變?yōu)槠呗曇綦A,行腔里多次出現(xiàn)Fa、Si兩音,行樂風(fēng)格與昆曲不似,更古樸典雅,且級進(jìn)較多。在民間,七聲為特征的【山坡羊】以北方弦索腔?4?曲牌【山坡羊】為代表,主要用于河南大弦戲、羅戲、二夾弦,山東柳子戲、大弦子戲、羅子戲,河北絲弦、四股弦,山西羅羅腔,安徽二夾弦,分布五省,方域集中。唱詞是齊言體上下句,結(jié)構(gòu)完整者由6對構(gòu)成,已具備板腔化特點(diǎn),可變化各種調(diào)式、板式,男女分腔,為一個(gè)完善的系統(tǒng)。在此,【山坡羊】曲牌意義淡化,板式變化之“腔”得以強(qiáng)化。音樂方面,弦索腔【山坡羊】典型結(jié)尾形態(tài)與南商調(diào)北詞2支【山坡羊】具有典型意義的第1句,以及1支北中呂【山坡羊】第1句結(jié)束句形態(tài)都有一定的相似性。下面將前二者做對比。(見譜例2)可見二者具有相同下行旋律框架,七聲羽調(diào)式特征。《九宮大成》中僅有的1支北中呂【山坡羊】與其他樂譜旋律格格不入,然而卻能找到與弦索腔旋律的關(guān)聯(lián),其結(jié)尾句與柳子戲《脫獄牢》趙匡美生角唱腔起腔三字頭、第1和第2句兩字中間拖腔具有相同旋律框架、調(diào)式與落音。這一相同旋律在唱腔中出現(xiàn)次數(shù)少,主要在唱腔原板部分,而過門中的這一旋律形態(tài)則更穩(wěn)定,成為一種固定的典型形態(tài),在每一句之間均出現(xiàn)(其中第8和第9句之間沒有過門),體現(xiàn)出穩(wěn)定意義。譜例2 《百花亭》【山坡羊】第1句和《脫獄牢》中趙匡美的生角唱腔【山坡羊】結(jié)束句三、?俗曲類【山坡羊】民間多元化發(fā)展
俗曲類【山坡羊】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就有多元性,沈德符《顧曲雜言·時(shí)尚小令》講到【山坡羊】自宣德、正統(tǒng)至成化、弘治之后流行于中原,《市井艷詞》中所載共19句的《熬?髻》為“牌名之冠”,被稱作“我明一絕”,“今南、北詞俱有此名,但北方唯盛愛【數(shù)落山坡羊】”?6?。顧起元《客座贅語·俚曲》講到“【山坡羊】有沉水調(diào),有數(shù)落,已為淫靡矣”。這一曲調(diào)同其他小曲一般,是“里弄童孺婦媼之所喜聞?wù)摺薄?/span>?7?由此可知【山坡羊】在明代的盛況,朗朗上口,婦孺皆知,且各種名字的【山坡羊】均有。據(jù)此推測,文獻(xiàn)描述中大流行的是各類民間俗曲【山坡羊】的概率更大。俗曲類【山坡羊】不同于文人創(chuàng)作的散曲和劇曲。其風(fēng)格多變,格律不規(guī)整,傳于市井,口語化鮮明,篇幅長大。《太古傳宗》之《弦索調(diào)時(shí)劇新譜》中有6首【山坡羊】:《掛枝兒》中的【訴落山坡羊】,《崔鶯鶯》《大王昭君》《小王昭君》《思凡》《孟哥兒》中的【山坡羊】各1支。俗曲【山坡羊】典型樂句擁有南曲類【山坡羊】同樣的旋律形態(tài)、框架與落音。同時(shí)還有自身特點(diǎn),包括詞格的大肆改變、固定過門的加入、唱腔詞樂的雙重世俗化、唱詞與樂句劃分的不統(tǒng)一、數(shù)板性質(zhì)樂段的加入、初步的板腔化特征等。在這幾支中,《思凡》【山坡羊】各地流傳最多,具體體現(xiàn)出不同的流變內(nèi)涵。(一)?《思凡》【山坡羊】及其多元化流變作為“時(shí)劇”,“思凡羊”本身具有來源的多元性及俗創(chuàng)的通俗性。時(shí)劇在最早的《太古傳宗》《納書楹曲譜》中出現(xiàn),這兩個(gè)譜集中的多數(shù)時(shí)劇在之后的昆曲譜本以及當(dāng)代各地民間音樂《集成》中早已不復(fù)存在。《思凡》之所以特別,緣于它后來“作為一個(gè)單折收錄在包括《遏云閣曲譜》……不下十余種知名曲譜中,且此后很多曲譜甚至直接將其稱為昆曲傳統(tǒng)曲目,可見《思凡》是時(shí)劇作品中昆化程度很高,在所有‘昆曲時(shí)劇’中影響深遠(yuǎn)的一出折子”?8?。筆者搜集樂譜時(shí)發(fā)現(xiàn)《思凡》在眾多劇種中流傳,除了昆劇,還作為粵劇牌子套曲、贛劇唱腔昆腔、東河戲漢腔類唱腔、祁劇唱腔、目連戲唱腔存見各地。它是連接雅化的“昆曲羊”與“俗曲羊”的紐帶,體現(xiàn)了頑強(qiáng)的生命力與流傳變異動(dòng)力。昆劇中的“思凡羊”共22句,與原始格律相比,“羊頭”依然保持7、7、7、8四句形式不變,第1、2、4句押韻的特征未變。“羊肚”部分?jǐn)U充較大,每句字?jǐn)?shù)不同。其中第11—16句進(jìn)行十分緊密,有學(xué)者認(rèn)為此處或許是從弋陽腔吸取“滾調(diào)”手法而成。?9?“羊尾”保持了以兩個(gè)“由他”引出的扇面對句,保留了南曲類【山坡羊】標(biāo)準(zhǔn)羊尾的2、5、2、5格律,把2個(gè)五字句分別擴(kuò)充為2句。從格律看,《思凡》中【山坡羊】仍為易于分辨格律的唱詞形態(tài),只是用了加入襯詞、擴(kuò)充“羊肚”和“羊尾”等方式,是民間俗曲【山坡羊】的體例,下面對比昆曲傳統(tǒng)唱段《玉簪記·問病》【山坡羊】、《思凡》【山坡羊】和《太古傳宗》中《掛枝兒》下句形態(tài)。(見譜例4)譜例4 《玉簪記·問病》【山坡羊】、《思凡》【山坡羊】第1句和《太古傳宗》中《掛枝兒》下句?10?(掃描文首二維碼)可見,“思凡羊”和“問病羊”旋律框架相同、板式不同,“思凡羊”樂曲風(fēng)格更明朗。其與《掛枝兒》有同樣的尾句形態(tài),可知“思凡羊”與“昆曲羊”“俗曲羊”之間的雙重關(guān)聯(lián)。從整體音樂形態(tài)框架與詞格來看,它較《掛枝兒》中的【山坡羊】與昆曲有更緊密關(guān)聯(lián),但脫離了“昆曲羊”形態(tài),發(fā)展出新的昆曲時(shí)劇形式【山坡羊】,對傳統(tǒng)唱詞格律、音樂形態(tài)與風(fēng)格等都有繼承和突破。在民間,“思凡羊”不全然屬于昆腔,有的反映出與昆腔“思凡羊”的關(guān)聯(lián),有的則完全不同。若以昆腔“山坡羊”為母體,可見不同劇種中“思凡羊”與其有不同程度的關(guān)聯(lián)。贛劇昆腔中的“思凡羊”?11?從形態(tài)看,與昆曲“思凡羊”除個(gè)別潤腔不同,其他并無差別,顯示出同為昆腔的直接照搬。粵劇昆腔中的“粵劇羊”?12?中加入地方樂風(fēng)的偏音Si,成為六聲音階,以此造成濃郁的廣東音樂風(fēng)格;具體的潤腔也有變化,在保留旋律框架與基本唱詞不變基礎(chǔ)上,加入語言的改變,樂曲風(fēng)格、潤腔、音階調(diào)式都變?yōu)榛泟邮剑w現(xiàn)出昆腔的地方性變化。安徽目連戲唱腔“思凡羊”?13?則變化較大,唱詞的形態(tài)同青陽腔,在詞體上并沒有出現(xiàn)典型的“羊尾”形態(tài),音樂主體不同于昆腔“思凡羊”,但前兩句依然為昆腔“思凡羊”的音樂形態(tài),體現(xiàn)出僅有前兩句對昆腔的借鑒模仿。此外,江西東河戲漢腔類唱腔?14?和湖南祁劇唱腔?15?則與昆曲“思凡羊”在唱詞和音樂形態(tài)上均不同,難以說明其是昆腔“思凡羊”的流變。上面五例代表了同劇目同名曲牌在民間生存的不同樣態(tài),借此我們可略窺俗曲類【山坡羊】曲牌在民間傳播的復(fù)雜性與多元性。正是“思凡羊”在昆曲中獨(dú)特的地位,與民間諸腔相融合的俗創(chuàng)理念,才使得其有如此之強(qiáng)的傳播與變化能力,不僅使得【山坡羊】在昆曲中的原始樣態(tài)得以俗化并向外傳播至其他劇種的“思凡羊”,而且作為一種雅俗之間的媒介影響著更多民間劇種與劇目。(二)?其他民間有流變關(guān)系的俗曲【山坡羊】民間俗曲類【山坡羊】的樣態(tài)十分多元復(fù)雜,有的還能看出曲牌標(biāo)志性頭、尾詞格,音樂有些許關(guān)聯(lián),有的則音樂有關(guān)聯(lián)但詞格完全看不出牌調(diào),更有大量同名異曲的存在。河北淶水南高洛村和北高洛村寶卷?16?音樂中的2支【山坡羊】,都具有這一曲牌的詞格特征,但與原始12句相比,多出1句,為13句,4句“羊尾”清晰可辨。音樂風(fēng)格上,由于是曲藝音樂中的唱段,每個(gè)樂句構(gòu)成較為簡單,重復(fù)性的樂句較多,二者是1支曲調(diào)的流變。二者第1句句尾的拖腔在兩個(gè)唱段中反復(fù)出現(xiàn),分別出現(xiàn)了4次,這一拖腔的形態(tài)讓人不難聯(lián)想到昆劇“思凡羊”中數(shù)次出現(xiàn)的典型拖腔。(見譜例5)譜例5 昆劇“思凡羊”典型句尾拖腔和《后土寶卷》句尾形態(tài)四、?器樂【山坡羊】的四層流變
明代器樂【山坡羊】已經(jīng)出現(xiàn),沈?qū)櫧棥抖惹氈飞暇黹_篇《曲運(yùn)隆衰》描述了兩種【山坡羊】,一種用結(jié) ? ? 語
從古至今的藝術(shù)續(xù)延中,不同類型的【山坡羊】展現(xiàn)了中國曲牌音樂發(fā)展中四種不同的形式與階段,即從南北曲曲牌及其形態(tài)變化,到曲牌的板腔化,以及曲牌的俗化,再到曲牌的器樂化。聚焦民間四種聲樂類型的【山坡羊】,可以看到“曲牌”概念中的嚴(yán)謹(jǐn)性與固定化逐漸瓦解的過程。昆腔【山坡羊】體現(xiàn)了嚴(yán)謹(jǐn)?shù)那聘拍睿乔埔魳纷顬楦叨劝l(fā)展時(shí)期的產(chǎn)物。詞格固定,文辭典雅,格律嚴(yán)謹(jǐn),音樂細(xì)膩,具有極度固定化、藝術(shù)化與雅化特征。然而,此種“高度”終而走向程式化、脫離大眾的弊端。此后,【山坡羊】找尋更適應(yīng)時(shí)代與審美需要的“俗化”路徑。高腔【山坡羊】沿著“向無曲譜,只沿土俗”生存法則,緊貼昆腔之態(tài),崇尚牌調(diào)之格,音樂形態(tài)呈現(xiàn)個(gè)體化差異,并有幫腔助唱等更平民化之變。由此,音樂風(fēng)格、牌體結(jié)構(gòu)、牌名含義開始求變。曲牌的板腔化體現(xiàn)在弦索腔【山坡羊】中,形成一種介于曲牌體與板腔體之間的曲牌發(fā)展階段,也是文人性質(zhì)的南北曲曲牌音樂走向民間的一條有效途徑。“曲牌”概念中原本固化的12句格律,演化成一種十二句體上下句詞格并加以板腔化。在此階段,所謂“曲牌”變成一種上下句“腔”的概念,即弦索腔系統(tǒng)多種板式、調(diào)式、分腔的變化,且“腔”的形態(tài)也在不斷發(fā)生各類變化,與高度固化的昆曲“曲牌”的概念構(gòu)成反向走勢,但其依然存在唱段繁冗、劇目嚴(yán)肅、拖腔較長等不善親民的跡痕。曲牌的俗化,【山坡羊】表現(xiàn)為散落在各種民間小戲中的曲牌樣態(tài)。這類曲牌不再有嚴(yán)謹(jǐn)詞格,通常短小,唱腔變化隨意。“曲牌”概念體現(xiàn)出更世俗化的特征,在一些短小的唱段中,“山坡羊”更傾向于一種雜曲小調(diào)的概念,結(jié)構(gòu)簡化至上下句或分節(jié)歌,靈活善用,通俗而利于傳唱。在民間展現(xiàn)的豐富生命力與原始“曲牌”意境差之千里。曲牌器樂化形成是在聲樂曲牌高度發(fā)展情況下產(chǎn)生的。在器樂曲牌向外傳播中,呈現(xiàn)不同層次流變模式,以戲曲伴奏形態(tài)為固定母體,經(jīng)歷了完整的10句至4句減至1句的流變,體現(xiàn)著音樂整體的不斷消融、內(nèi)核的廣泛存續(xù),反映了各地器樂曲牌傳播時(shí)的相互學(xué)習(xí)借鑒。【山坡羊】曲牌發(fā)展演進(jìn)的四種形式,正體現(xiàn)出中國曲牌音樂漫長歷史中的不同種類與階段。伴隨著從雅而俗步伐,我們看到“曲牌”的歷史演進(jìn)繁衍的進(jìn)程。責(zé)任編輯:田 ? ?薇 ?
腳注
1.?張春蕾:《曲牌【山坡羊】歷史發(fā)展的四種類型》,《中國音樂學(xué)》,2024年,第4期,第101-109頁。
2.?此表格中“正”表示正板,“贈(zèng)”表示贈(zèng)板,下同。
3.?譜例分別來自筆者根據(jù)《昆劇手抄曲本一百冊》記譜;石生朝、黎建明合著:《目連戲·南戲源流與聲腔形態(tài)研究》,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4年,第344頁;《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湖南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湖南卷》(上卷),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2年,第537頁;《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江蘇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江蘇卷》(下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2年,第1209頁;《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上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4年,第225頁。
4.?本文所言弦索腔,興于河南、山東一帶,由民間小戲發(fā)展而來,以明清俗曲為基礎(chǔ)。
5.?譜例分別見《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東卷》《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河南卷》。《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東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東卷》(上),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6年,第289頁;《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下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4年,第1898頁;《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河南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河南卷》(下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3年,第1434頁。
6.?〔明〕沈德符:《顧曲雜言·時(shí)尚小令》,載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三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第70頁。
7.?〔明〕顧元起:《客座贅語·俚曲》,載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二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第400-401頁。
8.?張品:《融匯諸腔、應(yīng)時(shí)而生——從〈思凡〉管窺“昆曲時(shí)劇”的音樂特征與歷史成因》,《天津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6年,第1期,第97頁。
9.?張品:《融匯諸腔、應(yīng)時(shí)而生——從〈思凡〉管窺“昆曲時(shí)劇”的音樂特征與歷史成因》,《天津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6年,第1期,第99頁。
10.?《問病》和《思凡》均為筆者根據(jù)《昆劇手抄曲本一百冊》譯譜,《掛枝兒》引自《太古傳宗》。
11.?《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江西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江西卷》(上冊),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9年,第112-114頁。
12.?《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廣東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廣東卷》(上),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6年,第270-272頁。
13.?《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上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4年,第214-217頁。
14.?《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江西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江西卷》(上冊),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9年,第583-586頁。
15.?《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湖南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湖南卷》(上卷),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2年,第504-506頁。
16.?《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河北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河北卷》(下冊),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5年,第2108、2134頁。
17.?譜例分別來自《寧海平調(diào)音樂》《中國戲曲志·浙江卷》《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浙江卷》《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廣西卷》。陳濤、胡利民編著:《寧海平調(diào)音樂》,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2年,第35頁;中國戲曲志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志·浙江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志·浙江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7年,第233頁;《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浙江卷》編輯部:《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浙江卷》(上冊),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1年,第631頁;《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廣西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廣西卷》(上冊),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2年,第299頁。
18.?〔明〕顧元起:《客座贅語·俚曲》,載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二集),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第618頁。
19.?筆者根據(jù)清代無名氏手抄工尺譜譯譜,工尺譜見板俊榮、張仲樵:《中國古代民間俗曲曲牌、曲詞及曲譜考釋》,南京: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3年,第149頁。
20.?《中國戲曲音樂集成》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河南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河南卷》(下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3年,第1301頁。
21.?《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安徽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安徽卷》(下冊),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7年,第1148頁。
22.?《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湖南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湖南卷》(下),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6年,第1298-1299頁。
23.?《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青海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青海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5年,第340-342頁;《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甘肅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甘肅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7年,第380頁。
24.?譜例分別見《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山東卷》《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陜西卷》《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河北卷》。《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山東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山東卷》(上卷),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4年,第249頁;《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陜西卷》編輯委員會(huì)編纂:《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陜西卷》(上冊),《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主編,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2年,第164頁;《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河北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河北卷》(下),北京:中國ISBN中心,1997年,第1368頁。
25.?譜例前二者為筆者根據(jù)海陸豐藝人鄭俊錦吹奏嗩吶與演唱工尺譜記譜。潮州市弦詩樂合奏曲【山坡羊】見《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廣東卷》。《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全國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廣東卷》編輯委員會(huì):《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廣東卷》(上冊),北京:中國ISBN中心,2006年,第684頁。
本文刊登于
《中國音樂》2025年第3期
民族音樂學(xué)與傳統(tǒng)音樂理論第69-79+199頁(總第193期)
……
免責(zé)聲明:【照片素材,版權(quán)屬于原作者,若涉及版權(quán)問題,請?jiān)髡呗?lián)系我們刪除處理,我們只做分享,不用于商業(yè)。】
來源:《中國音樂》編輯部
排版:陳 ? 旭
一審:虎延雙二審:姚? ?嵐
三審:齊 ? 琨
歡迎訂閱
訂閱方式
·可以通過郵局訂閱,郵發(fā)代號:2-263
中國標(biāo)準(zhǔn)連續(xù)出版物號:CN11-1379/J
·國外發(fā)行代號:Q986
國際標(biāo)準(zhǔn)連續(xù)出版物號:ISSN1002-9923
·可以通過識別任意二維碼在線訂閱
? 掃碼訂閱《中國音樂》
投稿方式
投稿網(wǎng)址:https://cmj.ccmusic.edu.cn
聯(lián)系方式
聯(lián)系電話:010-64887378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qū)安翔路1號中國音樂學(xué)院辦公樓303室
郵編:100101
申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費(fèi)
全國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工作辦公室
舉報(bào)電話:010-63098272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huì)主管
中國音樂學(xué)院主辦
中文社會(huì)科學(xué)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音樂類核心期刊
“中國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綜合評價(jià) AMI”核心期刊
“復(fù)印報(bào)刊資料”重要轉(zhuǎn)載來源期刊
RCCSE中國核心學(xué)術(shù)期刊(A+)
RILM收入期刊

![]()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fèi)查看免費(fèi)推送
- 南京招標(biāo)網(wǎng)
- 無錫招標(biāo)網(wǎng)
- 鎮(zhèn)江招標(biāo)網(wǎng)
- 蘇州招標(biāo)網(wǎng)
- 南通招標(biāo)網(wǎng)
- 揚(yáng)州招標(biāo)網(wǎng)
- 鹽城招標(biāo)網(wǎng)
- 徐州招標(biāo)網(wǎng)
- 淮安招標(biāo)網(wǎng)
- 連云港招標(biāo)網(wǎng)
- 常州招標(biāo)網(wǎng)
- 泰州招標(biāo)網(wǎng)
- 宿遷招標(biāo)網(wǎng)
- 樅陽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廣州奧天海鵬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 梅州梅縣華僑中學(xué)招標(biāo)網(wǎng)
- 無錫工程造價(jià)信息網(wǎng)
- 呼倫貝爾市人民政府
- 河北應(yīng)急廳
- 宿州公共資源交易網(wǎng)招標(biāo)
- 來賓招標(biāo)網(wǎng)
- 棚改招標(biāo)
- 陪標(biāo)出場費(fèi)一般是多少
- 東光縣財(cái)政局
- 南京政治學(xué)院
- 西南|采購網(wǎng)招標(biāo)公告
- 高陵區(qū)招標(biāo)
- 明光市工程建設(shè)招標(biāo)網(wǎng)
- 合川市信息網(wǎng)
- 撫順市建設(shè)工程招標(biāo)網(wǎng)
- 攝像機(jī)招標(biāo)
- 南皮縣教育局
- 臨汾招標(biāo)信息網(wǎng)
- 廣東建設(shè)網(wǎng)
- 中國科學(xué)院中關(guān)村醫(yī)院
- 海安政府招標(biāo)網(wǎng)
- 那曲招標(biāo)投標(biāo)公共服務(wù)平臺
- 永修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陜西招標(biāo)與采購網(wǎng)招標(biāo)公告
- 三沙市招投標(biāo)中心
- 招投標(biāo)收費(fèi)管理辦法
-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招標(biāo)信息公示網(wǎng)
- 秦皇島財(cái)政招標(biāo)
- 滎經(jīng)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寧夏工程建設(shè)招標(biāo)采購公共平臺
- 浙江省招投標(biāo)信息網(wǎng)
- 江蘇思源赫茲互感器有限公司
- 灤州市招投標(biāo)中心
- 保潔招標(biāo)公告
- 南師附中宿遷分校
- 濟(jì)陽縣招標(biāo)
- 北京市東城區(qū)花市小學(xué)
- 河南省政府采購網(wǎng)招標(biāo)投標(biāo)
- 鐵嶺市人民政府
- 陜西省招標(biāo)信息公示網(wǎng)
- 孟津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招投標(biāo)知識點(diǎn)和重點(diǎn)
- 云南機(jī)電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 天津美術(shù)學(xué)院
- 任丘市政府網(wǎng)
- 第|十三飛行學(xué)院
- 澠池縣人民政府
- 岱山教育網(wǎng)
- 金鄉(xiāng)招標(biāo)采購信息
- 營口招標(biāo)公司
- 廣西科聯(lián)招標(biāo)中心有限公司
- 揭陽招標(biāo)網(wǎng)
- 遼寧政府|采購招標(biāo)中心
- 招標(biāo)采購公司有哪些
- 南陽市高新區(qū)
- 嵩明縣人民政府
-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xué)
- 增城區(qū)財(cái)政局
- 電器采購招標(biāo)文件
- 銀行培訓(xùn)招標(biāo)
- 句容市教育局
- 定海區(qū)教育局
- 土購網(wǎng)|信息
- 涼城縣應(yīng)急管理局
- 徐州建筑招標(biāo)
- 采購管理ERP
- 安徽采購與招標(biāo)網(wǎng)
- 遼寧建設(shè)工程信息交易網(wǎng)
- 惠東縣惠東職業(yè)中學(xué)
- 陽谷縣教育局
- 四川政府采購網(wǎng)招標(biāo)采購
- 學(xué)校招標(biāo)文件
- 梅江區(qū)人民政府
- 遼陽招標(biāo)采購網(wǎng)
- 中煤陜西公司招標(biāo)網(wǎng)
- 單縣招標(biāo)網(wǎng)
- 施工總承包招標(biāo)文件
- 昆山招標(biāo)信息
-
 聯(lián)系客服
聯(lián)系客服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信息發(fā)布
信息發(fā)布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招標(biāo)訂閱
招標(biāo)訂閱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商機(jī)挖掘
商機(jī)挖掘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數(shù)據(jù)定制
數(shù)據(jù)定制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標(biāo)書代寫
標(biāo)書代寫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資質(zhì)辦理
資質(zhì)辦理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投標(biāo)咨詢
投標(biāo)咨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證書查詢
證書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綠色報(bào)告查詢
綠色報(bào)告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