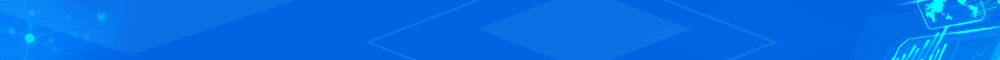高藝源|大型民族器樂協(xié)奏套曲《梨園》的詮釋研究
所屬地區(qū):北京 - 北京 發(fā)布日期:2025-05-28發(fā)布地址: 北京
大型民族器樂協(xié)奏套曲《梨園》的詮釋研究
高藝源
摘 ? ? 要:本文以賈達群的《梨園》為研究對象,運用普遍性詮釋學(xué)的四條基本原則——話語的雙重關(guān)系、理解和傳達的語言前提、理解的語法環(huán)節(jié)和心理環(huán)節(jié)、理解屬于重建對作品進行詮釋分析。結(jié)合跨學(xué)科視角,運用形式分析與意義闡釋的方法,從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形態(tài)結(jié)構(gòu)、音樂材料、文化映射等多個維度,探討作曲家如何融合現(xiàn)代作曲技法與傳統(tǒng)民族民間音樂語言,塑造《梨園》的音樂形態(tài)、體現(xiàn)“梨園”的文化意蘊,從而還原作曲家如何在這部描繪性連套作品中凸顯“梨園”本意。關(guān)鍵詞:賈達群;《梨園》;“梨園”;協(xié)奏套曲;普遍性詮釋學(xué)中圖分類號:J614.5?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9923(2025)03-0055-14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25.03.006作者簡介:高藝源(1998— ?),女,漢族,華東師范大學(xué)2023屆碩士畢業(yè)生,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音樂學(xué)院2023級在讀博士。本文為《中國音樂》編輯部舉辦的“第五屆音樂學(xué)碩博研究生優(yōu)秀學(xué)位論文評選”獲獎碩士論文。
基金信息:本文為202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shù)學(xué)重大項目“中國特色作曲理論體系研究”(項目編號:21ZD17)的階段成果。
An Interpretive Study of the Large-scale Chinese Instrumental Concerti Suite?The Operatic Circle
○Gao Yiyuan
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Jia Daqun's?The Operatic Circle?through the lens of Allgemeine Hermeneutik, employing its four fundamental principles—the dual relationship of discourse, the linguistic foundations of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the grammatical and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mprehension, and the reconstructive nature of interpretation—to rigorously analyze the work. Adopt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combines formal analysis with hermeneutic inquiry,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s multiple facets of the suite, including its creative genesis, structural design, musical lexicon,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how the composer harmoniously integrates modern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with traditional ethnic and folk musical idioms to forge a distinctive musical form that not only embodi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Operatic Circle" but also reaffirms its original artistic intent.
Keywords:?Jia Daqun;The Operatic Circle;"Traditional Operatic Circle";Concerti Suite;Allgemeine Hermeneutik
引 ? ? 言
作曲家賈達群于2018—2019年創(chuàng)作了大型民族器樂協(xié)奏套曲《梨園》。這部作品巧妙地將“協(xié)奏曲”體裁形式與中國傳統(tǒng)戲曲文化融合,呈現(xiàn)出復(fù)雜的結(jié)構(gòu)和深厚的文化內(nèi)涵。近年來,學(xué)界已從曲式結(jié)構(gòu)、體裁創(chuàng)新和審美意義等多個角度對《梨園》進行了研究。例如,李詩原運用賈達群的詩學(xué)策略和音樂理論,揭示并闡釋了作品中的審美、人文意義;郭三剛和蘇瀟、譚森聚焦于音樂形式,分析其結(jié)構(gòu)組合特征和形式生成邏輯;原晉彪則剖析了作品中的戲曲元素,揭示了文本符號化的表達策略。盡管現(xiàn)有研究在形式分析與符號表征領(lǐng)域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對作品形式象征意義的系統(tǒng)性闡釋仍有待進一步探索和深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如何透過詮釋學(xué)的視角,結(jié)合客觀的作曲技術(shù)理論分析與主觀的審美意象解讀,深入揭示《梨園》的音樂結(jié)構(gòu)與文化意蘊的多維關(guān)系,從而對作品進行更全面的理解。詮釋學(xué)作為一種探索作品多重文化意蘊的有效工具,已在音樂研究中得到廣泛應(yīng)用。20世紀末,于潤洋率先揭示了詮釋學(xué)在音樂研究中的潛力,提出通過“異質(zhì)同構(gòu)”的詮釋方法彌合形式與內(nèi)容的隔閡,從而提升音樂分析的深度與廣度。?1?克拉默(Kramer)則進一步強調(diào),音樂詮釋研究的終極目標是達到對作品意義的全面理解。?2?在此基礎(chǔ)上,一些學(xué)者進一步提出,音樂作品的分析不僅應(yīng)關(guān)注形式的建構(gòu),而且應(yīng)結(jié)合文化語境進行更為細致的闡釋。例如,鄭艷嘗試建立起一種“從文本解釋到意義闡釋”的研究框架?3?,通過融匯結(jié)構(gòu)分析與文化解讀的方式,為音樂作品的多維度理解提供了新的視角。基于上述研究的啟發(fā),本文將結(jié)合音樂的形式分析與審美詮釋來探討《梨園》的多重文化意義。在具體操作上,筆者將借鑒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提出的詮釋學(xué)四大原則,并結(jié)合客觀的作曲技術(shù)理論分析,開展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第一,話語的雙重關(guān)系;第二,理解的語法(grammatical)?4?與心理(psychological)?5?環(huán)節(jié);第三,文本與文化的互動;第四,理解的重建。通過這種方法力圖在“‘看(文本)、聽(音響)、說(意義)’中達到‘視域融合’”?6?。這種方法不僅繼承并擴展了音樂詮釋學(xué)的研究模式,而且通過整合客觀的作曲技術(shù)理論分析與主觀的審美意象解讀的方式為音樂形式分析開辟一條新的路徑,從而進一步豐富作品意義的多維度闡釋。一、?音樂文本的詮釋理路
1960年,伽達默爾(Gadamer)在著作《真理與方法》中提出了“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7?、“效果歷史”(effective history)?8?等詮釋學(xué)重要概念,“將詮釋學(xué)從認知性理解的方法論體系轉(zhuǎn)向一種新型的本體論學(xué)說”?9?。然而,他所建立的本體論詮釋學(xué)并非本研究的關(guān)注重點。本研究將詮釋視為一種技藝,期望它能為音樂的分析提供一個別樣視角,幫助我們關(guān)注到文本背后的意義。帶著這樣的目標溯源后發(fā)現(xiàn),19世紀初期,哲學(xué)家、詮釋學(xué)家施萊爾馬赫提出了一種適用于所有語言經(jīng)驗的普遍性詮釋學(xué)。他的詮釋研究方法論綜合了文本的語法和心理兩個視角,為解讀文本意義提供了具體路徑。從他所設(shè)定的詮釋規(guī)則來看,詮釋應(yīng)順沿以下四條原則展開:第一,每一種話語都具有雙重的關(guān)系;第二,理解和傳達以語言或文本為前提;第三,理解只在語法與心理兩個環(huán)節(jié)發(fā)生;第四,理解屬于重建。?10從這四條原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詮釋的目的就是重建文本的意義,而音樂作品作為一種特殊的文本,近似于一種完整的語言,作曲家是它的創(chuàng)造者。分析者的詮釋行為,實質(zhì)上是在了解作品與作曲家的基礎(chǔ)上,對音樂進行重建。將這些原則對應(yīng)到音樂分析的具體過程中,可以細分出以下四個分析步驟。(見圖1)二、?音樂的形式認知:基于戲曲及地域意象構(gòu)建的音高設(shè)計分析
下文的分析將結(jié)合第二、第三條原則展開——音樂的理解以形式結(jié)構(gòu)為前提并建立在形態(tài)的認知之上,將厘清《梨園》文本中基本動機和材料的來龍去脈(文本),探索核心動機自身的特色與作曲家的個性化表達(心理),以完成對作品表達形式內(nèi)容和接受理解方面的詮釋。《梨園》共包含四部協(xié)奏曲,它們分別以四種傳統(tǒng)戲曲劇種為表達主題,塑造了一個音響空間中的梨園意象,表達了作曲家的精神家園。第一樂章《序曲·梨園鼓韻》選用川劇主題,著力描繪巴蜀風土人情;第二樂章《隨想曲·梨園竹調(diào)》選用昆曲主題,在當代管弦樂織體下,展現(xiàn)梨園戲班中發(fā)生的悲歡離合;第三樂章《即興曲·梨園弦詩》選用京劇主題,在線性思維的基礎(chǔ)上,展現(xiàn)京劇的唱腔與韻味;第四樂章《狂想曲·梨園腔魂》選用秦腔主題,以具有代表性的傳統(tǒng)聲腔,描繪西北與黃土高原的遼闊地景。四部協(xié)奏曲相互結(jié)合共同鑄造了一個梨園景觀,還原了梨園戲班中的唱念做打。(一)?川劇引領(lǐng)架構(gòu):《序曲·梨園鼓韻》分析在第一樂章《序曲·梨園鼓韻》中,賈達群以川劇為主要的引領(lǐng)架構(gòu),依次選用昆腔、高腔、胡琴腔、彈戲四種代表性聲腔,并將它們轉(zhuǎn)化為該樂章的主題動機。這一轉(zhuǎn)化過程正是“視域融合”的具體體現(xiàn),即作曲家將川劇這一傳統(tǒng)藝術(shù)形式的多重聲音元素融入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之中,通過音樂語言的“對話”,形成了新的文化共鳴。在此過程中,川劇鑼鼓經(jīng)作為不同聲腔間的連接與裝飾,不僅在形式上實現(xiàn)了多聲腔的融合,而且在文化視域上實現(xiàn)了傳統(tǒng)與當代、地方性與普遍性的多重融合。(見表1)表1 第一樂章《序曲·梨園鼓韻》的主題動機(掃描文首二維碼)第一樂章中的鑼鼓經(jīng)材料近似于傳統(tǒng)鑼鼓經(jīng)【一字青板】?12?,作曲家將該曲牌中的小鑼替換為堂鼓,在音色上對該材料進行了個性化處理。此外,堂鼓和板鼓之間不斷地進行著交替與重疊,不僅在節(jié)奏與結(jié)構(gòu)的變化中延續(xù)了川劇鑼鼓“半臺鑼鼓半臺戲”?13?的傳統(tǒng),而且回應(yīng)了傳統(tǒng)在當代語境中的再創(chuàng)造。從第43小節(jié)開始,從四種聲腔轉(zhuǎn)化而來的材料紛沓而至。第45—46小節(jié),高腔主題動機出現(xiàn)在吹管樂組,尤其是高音嗩吶部分。這里的音高組合近似于【梁州序】?14?,作曲家將高音嗩吶與彈撥樂組結(jié)合,重現(xiàn)了傳統(tǒng)高腔“一人啟口,眾人相隨”的演唱形式。這種處理不僅在音色上體現(xiàn)了對傳統(tǒng)的忠實,還通過現(xiàn)代思維賦予了其新的表現(xiàn)維度。第45—47小節(jié),昆腔主題出現(xiàn),在二流板的音高框架下加入了大量的滑音,強化了潤腔效果,突出了聲腔的多變以及字少腔多的特征。彈戲主題動機則首次出現(xiàn)在第67— 69小節(jié)的彈撥樂部分。該動機高度源自彈戲“苦皮”?15?,在音高的選擇上“避工重凡”,苦戲中常見的七字句“二二三”的變體“二二六”作為基本的語匯構(gòu)成了該動機。胡琴腔主題動機首次出現(xiàn)在第126 —131小節(jié)的弦樂部分,以近似【夾夾板】?16?的模式進行,并進行了長短腔的處理,與梆笛部分的高腔素材變體形成對談。作為該樂章的關(guān)鍵線索,鑼鼓經(jīng)材料不僅在結(jié)構(gòu)上串聯(lián)了這四種不同川劇聲腔,而且在意義上搭建了跨越歷史層次的文化對話平臺。綜上,第一樂章《序曲·梨園鼓韻》通過五種簡潔凝練的核心材料動機構(gòu)建了豐富的音樂語境。這些動機不僅傳遞出川劇聲腔的獨特聲韻,而且通過節(jié)奏和音色的多重變化,使這一文化在當代音樂語境中煥發(fā)出新的生命力。(二)?昆曲及塞北江南引領(lǐng)架構(gòu):《隨想曲·梨園竹調(diào)》分析在《梨園》第二樂章《隨想曲·梨園竹調(diào)》中,作曲家通過對昆曲文化與江南音樂元素的深入挖掘,創(chuàng)造了一種跨越時空的聲音對話。作為中國傳統(tǒng)梨園戲曲音樂,昆曲具備著獨特的音樂表現(xiàn)力和深厚的民俗文化內(nèi)涵并已成為中國南方地區(qū)的一種重要文化符號。(見表2)表2 第二樂章《隨想曲·梨園竹調(diào)》的主題動機(掃描文首二維碼)在這一樂章中,作曲家通過音高主題的設(shè)計,巧妙地體現(xiàn)了昆曲音調(diào)的程式化特征。據(jù)魏良輔在《曲律》中所述,昆曲“五音以四聲為主”?17?,從四聲發(fā)展而來的“Re Do La”音型在昆曲曲牌中頻繁出現(xiàn),成為一種主腔音調(diào)。?18?該主題動機首次在第48—50小節(jié)出現(xiàn),經(jīng)過一次向上小三度的模進后以典型的主腔音調(diào)結(jié)尾。在第9 —16小節(jié),竹笛獨奏運用了“疊腔”“三疊腔”和“豁腔”等技法,生動地模擬出昆曲韻白中的人聲唱腔,為旋律增添了如泣如訴之感的同時還使器樂呈現(xiàn)出人聲化音色,從而在音色的塑造與情感的傳遞上,實現(xiàn)了昆曲與當代音樂表現(xiàn)形式的融合。江南絲竹主題動機在第75—76小節(jié)處引入。這段融合了昆腔“合頭”特征與江南絲竹的旋律,首次出現(xiàn)便持續(xù)了15個小節(jié),并在樂章的獨奏竹笛華彩樂段后再次出現(xiàn),強化了該樂章的整體連貫性。第二樂章通過對昆曲與江南音樂元素的借鑒與融合,展現(xiàn)了作曲家在當代語境中對這些傳統(tǒng)材料進行再創(chuàng)造。具體而言,樂章中器樂的人聲化詮釋,體現(xiàn)了音樂文本的抽象性與不精確性,各同源動機間視域的融合和對話則展現(xiàn)了作曲家對音樂結(jié)構(gòu)復(fù)雜性的巧妙把握。這一設(shè)計既“向后”追溯了傳統(tǒng)的昆曲文化,又“向前”彰顯了作曲家在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效果歷史”,在技術(shù)與文化層面實現(xiàn)了對昆曲藝術(shù)的標示與升華。(三)?京劇引領(lǐng)架構(gòu):《即興曲·梨園弦詩》分析第三樂章《即興曲·梨園弦詩》便是通過京劇主題發(fā)展而來。樂章中的三個主要音高動機分別為:京劇西皮聲腔主題、京劇二黃聲腔主題、京劇西皮過門主題。(見表3)表3 第三樂章《即興曲·梨園弦詩》的主題動機(掃描文首二維碼)京劇西皮聲腔主題動機出現(xiàn)在樂章的開頭,由獨奏二胡奏出。作曲家通過對弓法的特殊標注,使樂句從下弓開始,改變了它原有強弱旋律的同時還將旋律的起落變?yōu)椤把燮鸢迓洹保⑶以凇癆”“C”“?B”“E”四音上都標注了重音記號,模擬出西皮聲腔傳統(tǒng)的“一板一眼”板式。京劇二黃聲腔主題動機在第14—17小節(jié)首次呈現(xiàn)。這句旋律具有溫和的特質(zhì),速度較為平緩,且音程跨度較小,營造出一種人物內(nèi)省與思考的氛圍。可以依據(jù)黃金分割點進一步將其劃分為上下兩個不對稱的樂句。這種非對稱性不僅強化了樂句的內(nèi)在張力,而且進一步凸顯出二黃聲腔經(jīng)典的程式化表現(xiàn)手法。京劇西皮過門主題動機首次出現(xiàn)在第29小節(jié)。該動機從“G”音開始,并結(jié)束于“G”音,遵循宮—宮的運動路徑,忠實地再現(xiàn)了傳統(tǒng)西皮的板式特征。隨著音樂的展開,該動機不斷重復(fù),并以句間過門的形式貫穿整個樂章。通過這種方式,作曲家不僅強化了音樂結(jié)構(gòu)的連貫性和統(tǒng)一性,而且使傳統(tǒng)音樂材料不再僅作為歷史的“遺跡”存在,而成為該樂章音樂敘事的核心要素。(四)?秦腔及西北風情引領(lǐng)架構(gòu):《狂想曲·梨園腔魂》分析在《梨園》的第四樂章《狂想曲·梨園腔魂》中,作曲家以秦腔文化及富有西北地域特色的音樂文化為錨,架構(gòu)出獨特的西北風情,展現(xiàn)出秦腔的氛圍和韻味。第四樂章主要包含三類主題動機:秦腔苦音、花兒音樂、信天游音樂。(見表4)表4 第四樂章《狂想曲·梨園腔魂》的主題動機(掃描文首二維碼)第四樂章開篇,嗩吶奏響的秦腔苦音主題動機便奠定了全樂章的風格基調(diào)。該動機在E宮場域中,從“?F”向上跳進到“B”,并輔以“?D—E”的小二度滑音結(jié)束在“E”上,構(gòu)成了上行純四度后下行純五度的運動軌跡。該行進模式近似秦腔音樂中開口腔,復(fù)現(xiàn)了從商向上四度跳進到徵再落回至宮的典型苦音聲腔輪廓。?19?第9小節(jié)開始,音樂進入?E宮。此處,花兒音樂主題動機在中低音弦樂區(qū)展開,與秦腔苦音主題形成對位關(guān)系。該動機從商音出發(fā),在商—徵—羽—商的音列框架內(nèi)展開,呈示出較為完整的花兒框架。隨著樂章的發(fā)展,在第19小節(jié)處,信天游音樂主題動機以其標志性的七度大跳引入,并在連續(xù)三次再現(xiàn)中強化了秦腔悲涼的韻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該樂章出現(xiàn)了多次延長音,這樣的形式源自黃土高原上的拖腔演唱方式,在作品中它被賦予了新的表現(xiàn)力和情感內(nèi)涵。可以說,這樣的表達方式不僅是對歷史傳統(tǒng)的復(fù)現(xiàn),而且是傳統(tǒng)與當代的對話與延續(xù),重現(xiàn)出獨特地形環(huán)境下人與人之間交流時自然拖長音值的聲音圖景。三、?音樂的理解與重建:《梨園》意象
在上文的基礎(chǔ)上,本研究將結(jié)合詮釋的最后一條原則:分析者對音樂的理解屬于重建?20?,發(fā)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以施萊爾馬赫基于語言的共性和個性提出的“心理解釋”和“語法解釋”為方法論,從作品的觀念、形式程序以及觀念與形式程序?qū)?yīng)關(guān)系三個方面整體觀察作品中的邏輯關(guān)系,從而實現(xiàn)進一步的詮釋研究。(一)?心理解釋:文本意象映射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即使是同一種音樂類型,由不同的作曲家進行創(chuàng)作都會打上不同的個體烙印,從而形成個人的風格特征。心理解釋是一種詮釋類型,它主要關(guān)注文本含義的特殊性和個性,其“主要任務(wù)是理解作品的基本思想和作者的意圖”?21?。該視角可用于詮釋普遍的文本內(nèi)容,當然也可用于詮釋音樂作品。作品《梨園》描繪了一個聽覺世界中的梨園戲班,以第一人稱視角,展現(xiàn)了一種獨屬于人民的梨園文化。從它的音高材料和音樂的進行手法可以看出,每個樂章都存在兩組鮮明的對比。第一樂章中兩組對比意象分別是:觀園的作曲家主體、梨園的場景景觀。作曲家主體意象由高腔主題進行描繪,梨園意象則由鑼鼓經(jīng)主題、彈戲主題、昆腔主題、胡琴腔主題四種不同的材料加以塑造。樂章開篇,打擊樂組就以鑼鼓經(jīng)材料勾勒出具有川蜀韻味的梨園景觀。之后,觀園作曲家意象在作品第45小節(jié)處首次出現(xiàn)。當其在第179—181小節(jié)第二次呈示時,兩種不同的意象各自從原本模式中脫離出來,交織成復(fù)線條式的綜合音響姿態(tài)。觀園主體角色與梨園景觀意象交織,生成蒙太奇的景觀效果。在第三次呈示時,觀園作曲家五音動機被拉寬一倍,并加入節(jié)奏式與音高式潤腔變化,由梆笛在E宮上演奏。最終,在旋律不斷地變奏、展衍下,弦樂組的高胡、二胡和中胡以支聲復(fù)調(diào)的織體形式,以觀園作曲家意象材料為骨干音框架,在節(jié)奏和旋律走向上呈現(xiàn)多聲形態(tài)與景觀意象相互融合。(見圖3)可以說,作曲家主體與梨園景觀之間的音樂互動正是“視域融合”的體現(xiàn)。作曲家在傳統(tǒng)戲曲元素和自身主體意識之間建立起了深層次的對話,二者的相遇并不僅僅是單純的對比,而是通過音樂手法實現(xiàn)了對文化的再詮釋。這兩種視域在音樂中相互碰撞、交織,最終通過音高材料、織體結(jié)構(gòu)等手法實現(xiàn)了新的意義生成。結(jié) ? ? 語
音樂創(chuàng)作不僅僅是形式的構(gòu)建過程,而且是創(chuàng)作主體融入生命體驗的過程。正如賈達群所言,音樂就是音樂家用他自己的方式,并通過音響(這個音響不是隨便的音響,而是有組織的音響)這個媒介來重塑世界,以表達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各種關(guān)系和情感的過程。?28生命體驗具有普遍性,即便是他者的生命體驗,也在作品中有所映射。基于施萊爾馬赫提出的詮釋學(xué)四條原則,分析《梨園》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音樂文本中的“梨園”文化標識與文人精神表達:第一,基于傳統(tǒng)梨園文化的作曲家個性化闡述。從第一條原則“話語的雙重關(guān)系”出發(fā),發(fā)現(xiàn)賈達群的音樂創(chuàng)作與他在音樂結(jié)構(gòu)研究方面的詩學(xué)策略緊密相扣。作品體現(xiàn)了其理論與實踐的高度融合,散發(fā)著理性之光。第二,基于戲曲程式化原則建構(gòu)音樂文本形態(tài)結(jié)構(gòu)。根據(jù)第二、三條原則“理解的語法與心理環(huán)節(jié)”。本研究通過分析音樂形態(tài)結(jié)構(gòu)及音響的呈現(xiàn)形態(tài),探究了音樂形式中梨園文化景觀塑造的具體方式,識別了作曲家的藝術(shù)創(chuàng)新。《梨園》在音樂文本建構(gòu)過程中,使用了川劇、昆曲、京劇和秦腔四種傳統(tǒng)戲劇的原生符號與特質(zhì)性元素,但在音(核心材料的原初樣式)—音(核心材料在作品中的形態(tài)樣式)的過程中形成了個性化表達,賦予了作品獨特的梨園韻味。第三,在音樂文本中重建梨園圖景。根據(jù)第四條原則“理解的重建”,本研究在“心理解釋”和“語法解釋”兩條路徑下,探究了“梨園”音樂觀念與作品形式化程序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發(fā)現(xiàn)協(xié)奏套曲體裁在形式上結(jié)合了西方傳統(tǒng)奏鳴套曲曲式規(guī)范與中國傳統(tǒng)戲曲結(jié)構(gòu)程式;在內(nèi)容上四樂章前后分別以弋陽腔(川劇)、昆山腔(昆曲)、皮黃腔(京劇)、梆子腔(秦腔)為表達主題,以時間為軸線建構(gòu)了梨園戲曲的發(fā)展史。作品的主題不僅決定了音樂形式化過程、技巧和邏輯,而且進一步體現(xiàn)了音樂的深層意義。《梨園》立足于中國傳統(tǒng)梨園文化,在表現(xiàn)“梨園”文化內(nèi)涵的同時,也體現(xiàn)了理性創(chuàng)作思維和中西藝術(shù)的融合。作品為中國民族管弦樂的發(fā)展注入了新鮮血液,形成了獨特的音樂語言與全新的音樂體裁協(xié)奏套曲,在當代音樂組織探索中為中華傳統(tǒng)梨園文化賦予了新的時代內(nèi)涵和生命力。綜上所述,本文通過結(jié)合作曲技術(shù)的客觀分析與審美意象的主觀解讀,進一步探索了實證主義與詮釋學(xué)相融合的研究范式,并在施萊爾馬赫提出的詮釋原則基礎(chǔ)上,將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觀念與音樂文本自身的形式結(jié)構(gòu)相互聯(lián)系,以此實現(xiàn)“視域融合”。本文為《中國音樂》編輯部舉辦的“第五屆音樂學(xué)碩博研究生優(yōu)秀學(xué)位論文評選”獲獎碩士論文。責任編輯:田 ? ?薇 ?
腳注
1.?于潤洋:《釋義學(xué)與現(xiàn)代音樂美學(xué)(上)》,《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1990年,第4期,第25-31頁;于潤洋:《釋義學(xué)與現(xiàn)代音樂美學(xué)(下)》,《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1991年,第1期,第25-36頁;于潤洋:《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xué)分析(上)》,《音樂研究》,1993年,第1期,第39-53頁;于潤洋:《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xué)分析(下)》,《音樂研究》,1993年,第2期,第86-100頁。
2.?Lawrence Kramer. Musicology and Meaning.?The Musical Times, 2003, Vol.144, No.1883, pp.6-12.
3.?鄭艷:《從文本解釋到意義闡釋——賈達群〈第二弦樂四重奏:云起〉研究》,《中國音樂》,2022年,第5期,第134-143頁。
4.?語法是指對話語意義的貢獻取決于它所使用的語言的一般結(jié)構(gòu)。
5.?心理是指對話語意義的貢獻取決于個體作者或創(chuàng)作者的思想。
6.?鄭艷:《從文本解釋到意義闡釋——賈達群〈第二弦樂四重奏:云起〉研究》,《中國音樂》,2022年,第5期,第143頁。
7.?“視域融合”指解釋者在解讀文本時,將自己的主觀前見、個人經(jīng)驗和文本內(nèi)容的視域相互交織,共同揭示文本的意義。
8.?“效果歷史”指歷史事件或文化現(xiàn)象在不同時間點上對后續(xù)理解產(chǎn)生的影響。
9.?潘德榮:《西方詮釋學(xué)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第500頁。
10.?〔德〕費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詮釋學(xué)講演(1819—1832)》,洪漢鼎譯,載洪漢鼎主編:《理解與解釋——詮釋學(xué)經(jīng)典文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第50-52頁。
11.?賈達群:《音樂結(jié)構(gòu)研究的詩學(xué)策略》,《藝術(shù)百家》,2014年,第4期,第132-135、144頁。
12.?【一字青板】曲牌主要以四拍子的形態(tài)呈示,且伴有兩小節(jié)的弱起。該曲牌由小鑼、鉸子、大鑼、大鈸、小鼓、板六種打擊樂器演奏。
13.?沙梅:《川劇鑼鼓研究》,《音樂研究》,1996年,第2期,第57頁。
14.?該曲牌以地方的名字——梁州命名,后成了一類高腔中常用曲牌名。凡是屬于思念、悲苦的感情,都常用到這個曲牌。
15.?“苦皮”主要展現(xiàn)凄苦哀怨的情緒,腔調(diào)進行時“避工重凡”,少用傳統(tǒng)清樂七聲調(diào)式中的角和羽,多用清角和變宮。
16.?【夾夾板】:二拍子,屬于一板一眼。
17.?〔明〕魏良輔:《曲律》,載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5頁。
18.?周來達:《試論昆曲主調(diào)》,《音樂與表演》,2017年,第2期,第111-124頁。
19.?劉正維:《皮黃腔的個性》,《黃鐘》,2004年,第4期,第45頁。
20.?這里所述的“重建”是一種對作品的重新認識,它的目的不是去理解作曲家的意圖,而是基于音樂文本,從創(chuàng)作層面,借用作曲理論,音樂分析研究音樂文本。
21.?牛文君、彭啟福:《施萊爾馬赫和伯艾克對詮釋學(xué)方法論的不同建構(gòu)》,《天津社會科學(xué)》,2012年,第1期,第36頁。
22.?牛文君、彭啟福:《施萊爾馬赫和伯艾克對詮釋學(xué)方法論的不同建構(gòu)》,《天津社會科學(xué)》,2012年,第1期,第36頁。
23.?賈達群:《結(jié)構(gòu)分析學(xué)導(dǎo)引》,《音樂藝術(shù)》,2004年,第1期,第27頁。
24.?賈達群:《賈達群 大型民族器樂協(xié)奏套曲〈梨園〉·總譜》(共四冊),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9年。所引用的文字在譜本中,未標注頁碼。
25.?向延生主編:《中國近現(xiàn)代音樂家傳》(第四卷),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545頁。
26.?賈達群:《賈達群 大型民族器樂協(xié)奏套曲〈梨園〉·總譜》(共四冊),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19年。所引用的文字在譜本中,未標注頁碼。
27.?何為:《戲曲音樂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第473頁。
28.?賈達群:《作曲與分析的詩學(xué)策略——賈達群教授講座實錄》,《天津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17年,第4期,第5頁。
本文刊登于
《中國音樂》2025年第3期
作曲理論與作品分析第55-68頁(總第193期)
……
免責聲明:【照片素材,版權(quán)屬于原作者,若涉及版權(quán)問題,請原作者聯(lián)系我們刪除處理,我們只做分享,不用于商業(yè)。】
來源:《中國音樂》編輯部
排版:陳 ? 旭
一審:虎延雙二審:姚? ?嵐
三審:齊 ? 琨
歡迎訂閱
訂閱方式
·可以通過郵局訂閱,郵發(fā)代號:2-263
中國標準連續(xù)出版物號:CN11-1379/J
·國外發(fā)行代號:Q986
國際標準連續(xù)出版物號:ISSN1002-9923
·可以通過識別任意二維碼在線訂閱
? 掃碼訂閱《中國音樂》
投稿方式
投稿網(wǎng)址:https://cmj.ccmusic.edu.cn
聯(lián)系方式
聯(lián)系電話:010-64887378
電子郵箱:[email protected]
地址:北京市朝陽區(qū)安翔路1號中國音樂學(xué)院辦公樓303室
郵編:100101
申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費
全國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工作辦公室
舉報電話:010-63098272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主管
中國音樂學(xué)院主辦
中文社會科學(xué)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音樂類核心期刊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xué)綜合評價 AMI”核心期刊
“復(fù)印報刊資料”重要轉(zhuǎn)載來源期刊
RCCSE中國核心學(xué)術(shù)期刊(A+)
RILM收入期刊

![]()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查看免費推送
- 樅陽縣招投標中心
- 廣州奧天海鵬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 梅州梅縣華僑中學(xué)招標網(wǎng)
- 無錫工程造價信息網(wǎng)
- 呼倫貝爾市人民政府
- 河北應(yīng)急廳
- 宿州公共資源交易網(wǎng)招標
- 來賓招標網(wǎng)
- 棚改招標
- 陪標出場費一般是多少
- 東光縣財政局
- 南京政治學(xué)院
- 西南|采購網(wǎng)招標公告
- 高陵區(qū)招標
- 明光市工程建設(shè)招標網(wǎng)
- 合川市信息網(wǎng)
- 撫順市建設(shè)工程招標網(wǎng)
- 攝像機招標
- 南皮縣教育局
- 臨汾招標信息網(wǎng)
- 廣東建設(shè)網(wǎng)
- 中國科學(xué)院中關(guān)村醫(yī)院
- 海安政府招標網(wǎng)
- 那曲招標投標公共服務(wù)平臺
- 永修縣招投標中心
- 陜西招標與采購網(wǎng)招標公告
- 三沙市招投標中心
- 招投標收費管理辦法
-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招標信息公示網(wǎng)
- 秦皇島財政招標
- 滎經(jīng)縣招投標中心
- 寧夏工程建設(shè)招標采購公共平臺
- 浙江省招投標信息網(wǎng)
- 江蘇思源赫茲互感器有限公司
- 灤州市招投標中心
- 保潔招標公告
- 南師附中宿遷分校
- 濟陽縣招標
- 北京市東城區(qū)花市小學(xué)
- 河南省政府采購網(wǎng)招標投標
- 鐵嶺市人民政府
- 陜西省招標信息公示網(wǎng)
- 孟津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招投標知識點和重點
- 云南機電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 天津美術(shù)學(xué)院
- 任丘市政府網(wǎng)
- 第|十三飛行學(xué)院
- 澠池縣人民政府
- 岱山教育網(wǎng)
- 金鄉(xiāng)招標采購信息
- 營口招標公司
- 廣西科聯(lián)招標中心有限公司
- 揭陽招標網(wǎng)
- 遼寧政府|采購招標中心
- 招標采購公司有哪些
- 南陽市高新區(qū)
- 嵩明縣人民政府
-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xué)
- 增城區(qū)財政局
- 電器采購招標文件
- 銀行培訓(xùn)招標
- 句容市教育局
- 定海區(qū)教育局
- 土購網(wǎng)|信息
- 涼城縣應(yīng)急管理局
- 徐州建筑招標
- 采購管理ERP
- 安徽采購與招標網(wǎng)
- 遼寧建設(shè)工程信息交易網(wǎng)
- 惠東縣惠東職業(yè)中學(xué)
- 陽谷縣教育局
- 四川政府采購網(wǎng)招標采購
- 學(xué)校招標文件
- 梅江區(qū)人民政府
- 遼陽招標采購網(wǎng)
- 中煤陜西公司招標網(wǎng)
- 單縣招標網(wǎng)
- 施工總承包招標文件
- 昆山招標信息
-
 聯(lián)系客服
聯(lián)系客服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信息發(fā)布
信息發(fā)布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招標訂閱
招標訂閱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商機挖掘
商機挖掘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數(shù)據(jù)定制
數(shù)據(jù)定制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標書代寫
標書代寫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資質(zhì)辦理
資質(zhì)辦理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投標咨詢
投標咨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證書查詢
證書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綠色報告查詢
綠色報告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