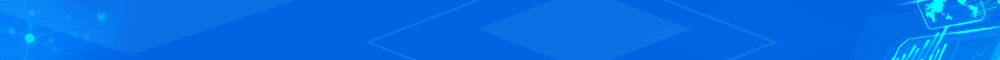陳林超:論停云室曲家及作品的戲曲史意義
所屬地區(qū):江蘇 - 無錫 發(fā)布日期:2025-05-20發(fā)布地址: 山西
創(chuàng)刊于1986年,2007年以來一直入選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集刊。
振興中華 ?繁榮戲曲
中 ? 國 ? 戲 ? 曲 ? 學 ? 會
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
論停云室曲家及作品的戲曲史意義*
Chen ?Linchao
陳林超
?簡
?介
陳林超,河南沁陽人,南京大學文學院戲劇與影視學專業(yè)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古典戲曲文獻、曲體格律。在《南大戲劇論叢》《戲曲研究》等刊物發(fā)表文章數(shù)篇,獲得中華戲劇學刊聯(lián)盟2023年度“青年優(yōu)秀論文獎”。
[摘 ?要]清初停云室主人王正祥和參與編纂的儲國珍,均可確定為宮廷戲曲教習。因此,停云室曲家及作品具有宮廷與民間的雙重屬性。停云室創(chuàng)作的《封神榜》不僅是宮廷和民間戲曲內(nèi)容與體制發(fā)展演進的重要參考,而且其編纂的理論著述,采用宮廷標準對民間戲曲聲腔、格律的規(guī)范,同時也反映了清初曲壇的實際情況。清代戲曲研究應(yīng)當關(guān)注以宮廷教習為紐帶,對宮廷與民間戲曲雙向交流的促進作用。特別值得關(guān)注的是,宮廷戲曲如何反饋、提升并影響民間戲曲的發(fā)展。
[關(guān)鍵詞]停云室 ?宮廷教習 ? 宮廷戲曲 ?民間戲曲 ?戲曲史
近些年來,隨著宮廷戲曲文獻的大量出版,宮廷戲曲成為戲曲研究中的一大熱門。眾所周知,宮廷戲曲與民間戲曲存在雙向的互動關(guān)系,但是,由于相關(guān)文獻的不足,研究者大多關(guān)注宮廷戲曲與民間戲曲的藝術(shù)分野,較少從特定群體角度探究二者互動的具體過程和影響因素。實際上,承應(yīng)于宮廷的民間藝人,是宮廷與民間戲曲交流的重要紐帶。清道光元年(1821)正月初一《恩賞日記檔》載:“今現(xiàn)在南府、景山外邊學生等,雖有三百余名,較比嘉慶四年之數(shù),不及其半,若承應(yīng)大戲等差,實不敷用。” [1]清代中后期,宮廷承應(yīng)演出的外學藝人仍有成百上千人。宮廷檔案還記錄了戲曲教習群體,他們活動于宮廷與民間,同民間戲班與藝人進行交往,并參與戲曲創(chuàng)作與出版活動,自然使宮廷與民間產(chǎn)生聯(lián)系,進而促進民間戲曲的發(fā)展。因此,宮廷教習這一特定群體,在清代戲曲發(fā)展史上十分值得關(guān)注。經(jīng)考證,筆者發(fā)現(xiàn)清代康熙年間的曲家王正祥、儲國珍,可確定為應(yīng)召入宮的宮廷戲曲教習,均有宮廷和民間的雙重身份。《中國古籍版刻辭典》載:“停云室:清康熙間茂苑(今蘇州市區(qū))人王正祥的室名。”[2]宮廷教習王正祥是停云室主人,儲國珍也參與停云室的編纂工作。因此,宮廷教習主導的創(chuàng)作和出版活動也具有宮廷和民間的雙重屬性。這一發(fā)現(xiàn)為進一步探索宮廷戲曲如何回歸并影響民間戲曲提供了重要的切入點。通過分析停云室的作品,可以更細致地研究與分析戲曲史相關(guān)階段的發(fā)展脈絡(luò)。
一、停云室曲家的雙重身份
現(xiàn)存停云室出版的作品有《十二律京腔譜》《十二律昆腔譜》《宗北歸音京腔譜》《宗北歸音昆腔譜》《音韻大全》《問奇一覽》,出版時間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此外,與之相關(guān)的尚有一冊題為“停云室新編《封神榜》”的劇作抄本。據(jù)停云室作品的落款者可知,其主要編纂者除了停云室主人王正祥(字瑞生)外,尚有蘇州盧鳴鸞(字南浦)、沈嗣連(字子畏)、宜興儲國珍(字君用)、無錫施銓(字均衡),均為江南人,就目前掌握的文獻來看,這四人除了參與停云室的創(chuàng)作工作外,未見其他曲學活動,為強調(diào)這一群體的價值,本文將停云室主人王正祥以及參與停云室創(chuàng)作工作的幾位曲家稱作“停云室曲家”。
停云室創(chuàng)作、出版的《十二律京腔譜》和《宗北歸音京腔譜》都是為北京的京腔所編纂的曲譜,王正祥等人為蘇州、無錫籍戲曲藝人,卻共同在北京編纂、出版京腔曲譜,由此推斷,幾人定然有在北京長期生活的經(jīng)歷。筆者在宮廷檔案中發(fā)現(xiàn),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月二十日“郎中費郎古等為宮廷用項開支銀兩的題本”中提到:“糊南府(音譯)所用戲臺架子……給教習王正祥絨纓子涼帽一,此項銀八錢。”康熙三十四年(1695)七月二十二日“李孝生等為宮廷用項開支銀兩的題本”與康熙三十七年(1698)六月初三日“尚之杰為宮廷用項開支銀兩的本”中均提到“教習初國珍”。[3]清初宮廷戲曲檔案現(xiàn)存數(shù)量較少,這幾條記錄彌足珍貴。檔案中提到的“教習王正祥”與停云室王正祥姓名相同、活動年代相同,兩條記錄“初國珍”的文獻其中一條提到了“鮑虎”,另一條提及“包虎”,筆者認為,“鮑虎”“包虎”應(yīng)為同一人,“包”是“鮑”的省寫,“儲國珍”亦省寫作“初國珍”。此外,筆者發(fā)現(xiàn),南京圖書館藏《宜興南臧儲氏分支譜》卷二記載“儲國徵”之名,其“字君用,號辰玉,內(nèi)廷供奉”,其孫出生于“康熙丙寅”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其父儲有慈下著錄“國徵徙居都中正陽門外陜西巷,今遷騾馬市榮子巷潘家沿河”[4]。根據(jù)家譜記載,宜興儲國徵字君用,遷居北京為宮廷戲曲藝人,停云室曲家儲國珍亦字君用,二者活動年代亦相同,當為同一人。家譜信息與宮廷檔案兩相印證,宜興儲國珍遷居北京成為宮廷戲曲教習,同時參與王正祥停云室的相關(guān)創(chuàng)作活動。宮廷檔案中記錄的“教習王正祥”僅為孤證,然而,儲國珍參與了王正祥“停云室”的編纂工作,其宮廷教習身份的確認,為王正祥宮廷教習的身份提供了重要佐證。雖然參與停云室創(chuàng)作工作的其他幾位曲家的身份信息暫時未能考證,但已確認停云室主人王正祥以及參與者之一儲國珍的宮廷教習身份。這些足以表明停云室與宮廷之間存在明確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停云室曲家及其作品無疑帶有一定的宮廷屬性。
莊清逸《南府之沿革》言:“供奉演劇者,皆太監(jiān),亦有外人,亦是承差人員,非業(yè)梨園者。”[5]民間戲曲藝人雖然被選入宮廷充當教習或演員,實質(zhì)上是民籍伶工,他們除承應(yīng)宮廷之外,主要生活在民間,從而與民間戲曲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停云室作品中多有提及停云室與民間的往來信息,《宗北歸音·序》:“歲之春仲,客自江上來者,相與質(zhì)證古今,偶以北曲之無定譜也,而折衷于予焉……譜成,予止存為備覽,無意付之梓人,詎意客之好事,引一剞劂氏至。”[6]序文中記錄了王正祥與友人的交往和談曲經(jīng)歷,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友人對停云室作品的編纂和出版提供了充分的鼓勵和支持。停云室作品面向民間出版,如今館藏數(shù)量較多,《十二律京腔譜》至少現(xiàn)存兩部抄本,也可說明該譜刊行后具有一定的傳播影響力。儲國珍的信息更為直觀。《宜興南臧儲氏分支譜》卷二明確記載儲國珍“徙居都中正陽門外陜西巷,今遷騾馬市果子巷潘家沿河”,可知儲國珍一類的宮廷教習在北京承應(yīng)于內(nèi)廷,居住和生活于民間。根據(jù)家譜的記載,儲國珍之子儲士銓“字翁宰,內(nèi)廷供奉……女二,長適湖廣通判王,次適養(yǎng)心殿侍衛(wèi)孫”,其孫儲廣“字育民,上苑院供奉,生康熙丙寅六月初八日”[7]。儲國珍子孫三代承應(yīng)宮廷,有著典型的家傳背景,其姻親關(guān)系亦體現(xiàn)出儲國珍在北京有著長期而廣泛的交際圈。因此,停云室曲家從江南被征召入宮,一方面承應(yīng)宮廷,一方面也有著清晰的民間生活線索。
以京劇的發(fā)展為例,可以管窺戲曲自民間入宮廷,而又重返民間的過程。“徽漢合流”是京劇形成的重要一環(huán),源于民間的戲曲劇種承應(yīng)宮廷需要傳入北京,進入宮廷,在內(nèi)廷形成符合宮廷審美的藝術(shù)形式,再傳至民間,從而促進京劇在北京生根發(fā)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8]有幸入宮承應(yīng)的戲曲藝人,自然成為民間觀眾追捧的對象,一些宮廷的演出形式和喜好也被民間戲曲奉為圭臬。清代宮廷人數(shù)眾多的外學戲曲藝人的生活軌跡也應(yīng)大致與停云室曲家相似。停云室曲家身份的確定,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化研究宮廷教習群體的新視角。雖然清宮外學藝人數(shù)量龐大,但像停云室曲家這樣在民間創(chuàng)作和出版劇作、曲譜及曲韻著作的藝人,目前所知仍然極少。停云室曲家及其作品對于民間戲曲的傳播和發(fā)展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
二、雙重身份影響下的劇本創(chuàng)作
自20世紀50年代起編纂的戲曲史著作中,宮廷戲曲已占據(jù)一席之地,其中略有述及宮廷戲曲與民間戲曲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周貽白的戲曲史著作論述宮廷戲曲與內(nèi)廷演劇較早較詳,并簡要提及宮廷對于民間戲曲的影響,如:“中國戲劇之演進,其本源雖然來自民間,但各朝代均有被征取至宮廷表演之事實,因而宮廷表演亦遂影響民間。”[9]此說強調(diào)了宮廷因素在民間戲曲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缺少具體文本,周著主要從觀念上描述了宮廷戲曲影響民間戲曲這一過程的表象特征,并未談及具體過程和方式。停云室創(chuàng)作的《封神榜》抄本為考察宮廷戲曲與民間戲曲提供了一個契機,停云室曲家雙重身份影響下的劇本創(chuàng)作具有值得挖掘的戲曲史價值。
(一)《封神榜》的作者和創(chuàng)作時間
停云室《封神榜》抄本現(xiàn)藏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卷首題“停云室新編封神榜全卷”,署“古吳南浦、茂苑嘯俠同筆”。吳曉鈴認為:“竊疑古吳南浦即盧鳴鸞,茂苑嘯俠為王正祥,二氏曾纂訂《十二律昆腔譜》及《十二律京腔譜》,并有康熙間停云室刊本。”[10]當是。停云室《封神榜》中的兩支曲文明確了其與王正祥停云室的關(guān)系,并提供了該劇創(chuàng)作年代的線索。停云室編纂的《十二律京腔譜》中【春霽】【秋霽】所選二曲注明出自《封神》,其曲文與停云室新編《封神榜》第十一出中【春霽】【秋霽】完全一致,二者均為“停云室”作品,參與編纂者都有王正祥和盧鳴鸞。《十二律京腔譜》刊刻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此,《封神榜》的創(chuàng)作年代無疑在此之前。《封神榜》中的一些細節(jié)或許有助于進一步推定該劇的創(chuàng)作時間。《封神榜》第一出《家宴》以慶賀升平、恭祝帝業(yè)為感情基調(diào),其中一曲為:
【節(jié)節(jié)高】君王國祚長,撫千方,青宮新立綸音降。蒼生望,四海揚,人歡暢。堪稱吾國成平象,黎民猶可相依仗。猶慚我輩少劻勷,無由展報君恩貺。[11]
此處在祝頌帝王時特地提及“青宮新立綸音降”,劇中念白亦云“天子新立東宮”,這一現(xiàn)象或許與其創(chuàng)作時間相關(guān)。停云室作品的出版時間較為集中,可見《封神榜》的創(chuàng)作時間上限應(yīng)距之不遠。據(jù)史實而言,康熙十四年(1675)十二月胤礽被冊立為皇太子,這是清代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公開建儲,對清廷而言是極為莊重的大事件,與此同時期的宮廷教習創(chuàng)作的劇本中對建儲事件的記錄和頌揚具有現(xiàn)實可能和政治需要。因此,《封神榜》所謂“新立東宮”之言,或許與康熙立儲相關(guān),本文認為,根據(jù)這一現(xiàn)象,可將《封神榜》的創(chuàng)作時間上限推定為康熙十五年(1676)。
(二)《封神榜》的雙重屬性
以往述及《封神榜》的研究多將其視作民間戲曲文本,這一認定有其合理性。《封神榜》的作者除承應(yīng)宮廷外主要在民間生活,他們創(chuàng)作的劇作自然也會在民間流傳,《封神榜·開宗》亦言及“《封神榜》先標大概,傳播在神京”[12],作品的傳播也正是作者的希冀。《十二律京腔譜》選錄《封神榜》【春霽】【秋霽】二曲作為例曲,該譜作為戲曲格律譜公開出版,序文中明言要規(guī)范民間世俗弋腔,其選錄停云室創(chuàng)作的《封神榜》作為例曲規(guī)范主要是自我標榜的宣傳手段,與沈自晉《南詞新譜》、張彝宣《寒山堂曲譜》的做法相同,這一行為也說明停云室有意推動《封神榜》的流傳。
王正祥的宮廷教習身份使其劇本創(chuàng)作帶有鮮明的宮廷色彩。停云室《封神榜》殘存目錄有“第二十一出”字樣,《開宗》前有“頭股”二字,這與昇平署戲曲抄本中常見的“頭本”“頭段”相同,是首本的標記。《封神榜·開宗》首曲【慶清朝】顯然具有歌頌清廷跡象,第一出《家宴》敘寫姬昌闔家歡聚景象,曲文著意渲染帝業(yè)升平,如【梁州新郎】合頭云:“憑杯酒,齊歡暢,愿民安物阜調(diào)豐象,歌帝力,共擊壤。”尾聲為:“君臣共樂升平象,祝黎民相生相養(yǎng),但愿得人沐和風德澤長。”[13]該劇甫一開場便是濃郁的粉飾太平盛世、恭祝帝業(yè)永昌的情感氛圍,且其歌頌文字與清宮承應(yīng)戲與連臺本戲如出一轍。對比《封神榜》與《封神天榜》可發(fā)現(xiàn),二劇第一本所敘情節(jié)脈絡(luò)和范圍大體一致,《封神榜》涉及大量神妖仙幻,演出難度較大,在舞臺搬演與主題特征上與宮廷大戲具有一致性。
(三)《封神榜》的雙重影響
《封神榜》是其后宮廷大戲《封神天榜》創(chuàng)作時的重要文本參考,后者大量內(nèi)容直接源于《封神榜》。以上述《封神榜》第一出《家宴》為例,該出在《封神天榜》中作《西伯侯樂宴思朝》,除幾處詞句有所修改外,《封神天榜》完全照搬《封神榜》的內(nèi)容,這不僅表明《封神榜》的內(nèi)容完全符合清宮宣傳教化的需要,也說明《封神榜》符合宮廷大戲開場和收煞的體制和內(nèi)容要求。《封神天榜》對《封神榜》的大量照搬或沿襲是《封神榜》宮廷影響的延續(xù)。
通過《封神榜》與《封神天榜》的文本對比可以明確《封神榜》的昆弋合演屬性。《封神天榜》對《封神榜》文本的因襲現(xiàn)象已有研究者指出,但未及深入探究其內(nèi)在聯(lián)系。[14]本文發(fā)現(xiàn),二劇文本異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劇本體制和聲腔歸屬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封神天榜·西伯侯樂宴思朝》一出注明昆腔,該出情節(jié)顯然更適合昆腔婉轉(zhuǎn)傳情,結(jié)合曲牌使用情況及曲律亦可佐證其所注昆腔屬實,該出曲文、念白照搬《封神榜·家宴》,據(jù)此可推知《封神榜·家宴》一出為昆腔。《封神天榜》注明弋腔的《奉玉敕女媧招妖》《聞邊警紂王遣相》《狐妖巧計殺中宮》與《封神榜》中《宣旨》《遣相》《遣妖》等出目的整出內(nèi)容基本一致,可見《封神榜》多出使用弋腔。《封神榜·勘問》中【風入松】【一江風】內(nèi)均注明加“滾”,《封神天榜》注明弋腔的對應(yīng)出目的二曲從之,且其加滾的位置相同、內(nèi)容相似,《封神榜》中【一江風】中有重唱曲文:“你把恩情一旦忘,你把恩情一旦忘,心中好慘傷,少不得死為厲鬼伸冤狀,少不得死為厲鬼伸冤狀。”[15]其中兩句重唱句與《十二律京腔譜》【一江風】例曲中重唱句位置、格式、格律完全一致,其他南曲曲譜均不存在這一重唱格,可見其為京腔(弋腔)所有。[16]這些現(xiàn)象證實《封神榜·勘問》一出確為弋腔,也佐證了《封神天榜》所注聲腔的真實性。因此,《封神榜》主體為弋腔連臺本戲,部分出目使用昆腔,該劇為昆弋合演劇目,雖然其昆弋合演的程度尚不如其后《封神天榜》之類的宮廷大戲成熟,但《封神榜》的昆弋合演連臺本戲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為其后宮廷大戲的創(chuàng)作導夫先路。
目前尚未有清初順治、康熙年間民間演出中采用昆弋合演的有關(guān)資料,以往研究中多認為北京民間演出中昆弋合演的出現(xiàn)大致在乾隆時期宮廷大戲創(chuàng)作之后,《中國戲劇史長編》言:“‘昆’‘弋’同班,尚為乾隆乙未前后的事。”[17]清乾隆五十年(1785)詔令云:“嗣后城外戲班,除昆、弋兩腔仍聽其演唱外,其秦腔戲班,交步軍統(tǒng)領(lǐng)五城出示禁止。現(xiàn)在本班戲子,概令改歸昆、弋兩腔。”[18]乾隆時期清廷僅允許民間昆、弋兩腔的演出,說明昆、弋兩腔歷來在民間具有深厚的演出基礎(chǔ),二者合演具有現(xiàn)實可能。乾隆時期的李光庭提及當時戲班時載:“時則有若宜慶、翠慶,昆、弋間以亂彈。”[19]這都證明乾隆年間北京民間昆弋合演已較為常見。康熙初年王正祥為代表的宮廷教習創(chuàng)作了昆弋合演的《封神榜》,并選入《十二律京腔譜》進行宣傳,這類宮廷教習創(chuàng)作的昆弋合演劇作,對民間戲曲昆弋合演的演出形式應(yīng)當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因此,北京民間演劇史上昆弋合演的出現(xiàn)時間或應(yīng)較目前界定的乾隆后期更早。
三、雙重身份影響下的理論著述
停云室創(chuàng)作、出版的作品多為曲律規(guī)范類著作,包括《十二律京腔譜》《十二律昆腔譜》《宗北歸音京腔譜》《宗北歸音昆腔譜》《音韻大全》《問奇一覽》,涵蓋了昆腔曲譜、京腔曲譜、曲韻、字書等十分全面的曲學內(nèi)容,這是目前罕見的確定為清初宮廷戲曲教習編纂、出版的著作。雙重身份的停云室曲家創(chuàng)作的理論著作,具有較為重要的文獻學意義和戲曲理論研究價值,借助這些材料可以探究宮廷戲曲與民間戲曲的體制差異、宮廷戲曲影響民間戲曲聲腔規(guī)范的具體途徑等。
(一)形式復古與內(nèi)容尚新
一方面,受宮廷音樂理念影響,停云室編纂的曲譜在形式上有著鮮明的尊崇古樂的特征。清代宮廷音樂有著崇尚古樂的傾向,復古思潮較為盛行,官方組織編纂了《御制律呂正義》《御制律呂正義后編》《古樂經(jīng)傳》《律呂闡微》《樂律表微》等樂律著作,深入探究古樂原理。官方組織編纂的《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也以恢復古樂體系為理論基礎(chǔ),其《分配十二月令宮調(diào)總論》言:“我圣祖仁皇帝考定元聲,審度制器,黃鐘正而十二律皆正,則五音皆中聲,八風皆元氣也。今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宮調(diào)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20]其中提及清康熙時期考定古樂理論和器樂,《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也延續(xù)了這一復古觀念,該譜將宮調(diào)搭配月令、五音,與傳統(tǒng)宮調(diào)曲譜體例有異。停云室編纂的曲譜正產(chǎn)生于康熙年間,幾部曲譜均拋棄傳統(tǒng)宮調(diào)體系而采用古樂理念,《十二律京腔譜》《十二律昆腔譜》以十二律分類曲牌,《宗北歸音京腔譜》《宗北歸音昆腔譜》以五音分類曲牌。《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提到康熙年間復興古樂后“十二律皆正,五音皆中聲”,在這一背景之下,宮廷教習組織編纂的曲譜選用古樂十二律、五音作為曲牌分類,其曲譜在形式上充滿了復古意蘊,這也是停云室的宮廷性質(zhì)的體現(xiàn)。
另一方面,停云室編纂的曲譜注重實用性,其內(nèi)容基本體現(xiàn)了清初曲壇的實際發(fā)展狀況。停云室編纂的曲譜最具使用價值的是兩種昆腔曲譜——《十二律昆腔譜》《宗北歸音昆腔譜》,這些曲譜出版后至今仍多見館藏,劉世珩暖紅室曾翻刻《十二律昆腔譜》,并經(jīng)吳梅校勘。現(xiàn)存清代南曲格律譜主要有《九宮正始》《九宮譜定》《寒山曲譜》《十二律昆腔譜》《南詞定律》《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等,其中《南詞定律》與《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為官修曲譜,編纂時間均晚于《十二律昆腔譜》。《九宮正始》《九宮譜定》《寒山曲譜》均以“尊元”為主要價值取向,追求南曲古本,而《十二律昆腔譜》開啟了崇尚實用之風,從歷時性的角度對前代曲譜進行訂正,將當時曲壇實際使用的曲牌句格確定為正格,因此與沈璟、沈自晉二譜顯示出格律方面的差異,其中許多做法得到了后世曲譜的認可和延續(xù)。例如,《十二律昆腔譜》將犯調(diào)曲牌單獨歸為一類,這一設(shè)定在其后《南詞定律》《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中均得到延續(xù);《十二律昆腔譜》是現(xiàn)存第一部列明曲牌聯(lián)套的南曲格律譜,在譜中列明曲牌聯(lián)套方式的做法,也被《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南北詞簡譜》沿用;《十二律昆腔譜》所選錄的部分曲牌格律較前人曲譜有所差異,但其后的《南詞定律》《九宮大成》均與之相同。整體來看,《十二律昆腔譜》所收曲牌格律大致體現(xiàn)了南曲句格的發(fā)展變化,并且得到了其后曲譜的認可和采用。《十二律昆腔譜》的諸多修訂既是對南曲格律的完善,也是對清初南曲格律的記錄,體現(xiàn)了該譜重要的曲學價值。《宗北歸音昆腔譜》記錄了昆腔北曲曲牌使用性質(zhì)、曲牌聯(lián)套方式、格律規(guī)范的發(fā)展變化,對昆腔北曲研究具有較為重要的參考價值。[21]
吳梅在《十二律昆腔譜跋》中稱贊道:“足為嘌唱家之先導,不獨詞學之功臣也。至其論律諸條,亦較舊譜為勝。”[22]停云室編纂的曲譜得到曲學名家吳梅的認可和贊揚。《十二律京腔譜》的傳世抄本、暖紅室對《十二律昆腔譜》的翻刻等行為,都是對停云室曲譜的肯定。停云室曲家的雙重身份使他們掌握了宮廷戲曲規(guī)范,也有助于其編纂的曲譜在民間的傳播接受,其對民間戲曲創(chuàng)作亦應(yīng)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宮廷弋腔與民間弋腔
根據(jù)《南詞敘錄》和《萬歷野獲編》等文獻的記載,明代萬歷年間,弋陽腔不僅在北京民間流傳,更開始進入了宮廷。民間的弋腔進入宮廷之后,受到宮廷環(huán)境和藝術(shù)要求的影響逐漸宮廷化,相較于民間的弋腔更為規(guī)范,這是弋腔自民間向?qū)m廷的流動。康熙帝曾提及:“近來弋陽亦被外邊俗曲亂道,所存十中無一二矣。”[23]這也進一步明確了宮廷與民間弋腔的區(qū)別。停云室曲家承應(yīng)內(nèi)廷,對宮廷弋腔較為熟稔,其編纂的《十二律京腔譜》是基于宮廷弋腔的標準對民間弋腔的規(guī)范,這是弋腔自宮廷向民間的流動。王正祥曾提及編纂京腔曲譜的原因:
乃若弋曲之與昆曲并行也,實行于未有昆腔之先,于今為盛。詞隱自藏其拙,竟不能定板核腔,而后人亦無有能著弋譜者,無怪乎世俗之弋曲,以信手之板為板,而以信口之腔為腔者也。頹波泛濫之下,不有砥柱于中流,詎不為詞壇欠事耶?[24]
從其強調(diào)“世俗之弋曲”可以看出,編者是站在宮廷弋腔的角度評價北京民間弋腔。停云室曲家對北京民間弋腔和宮廷弋腔都十分熟悉,他們以宮廷弋腔為標準對民間弋腔進行歸納和總結(jié),為京腔編纂了完整的板眼體系,總結(jié)了京腔“三腔三調(diào)”的腔調(diào)形式,并區(qū)分了京腔滾調(diào)的加滾、合滾兩種形式。宮廷弋腔在與昆腔合演中不斷向昆腔學習,因此較之民間弋腔更為規(guī)范,宮廷教習對這一情況更為熟悉,《十二律京腔譜》與《十二律昆腔譜》在編纂體例和文本、格律方面存在高度相似,該譜的創(chuàng)作也明顯參照了昆腔曲譜。
《十二律京腔譜》《宗北歸音京腔譜》的出版對京腔的發(fā)展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其后,“京腔”之名得到了廣泛認可,成為民間弋腔的專稱,《十二律京腔譜》現(xiàn)存清代抄本,亦可見其流傳與接受。京腔在乾隆年間發(fā)展至鼎盛時期,涌現(xiàn)出被稱為“京腔十三絕”的一批優(yōu)秀藝人和譽滿京城的“京腔六大班”演出團體。近人夏仁虎《舊京瑣記》中言:“都中戲曲,向惟昆、弋,弋腔音調(diào)雖與昆異,而排場詞句大半相同,尚近于雅。”[25]正是由于弋腔與昆腔一起躋身廟堂,使得宮廷弋腔,乃至受其影響的民間京腔,揚棄了弋陽腔的部分俚俗特征,而更為規(guī)范雅致。京腔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聲腔從民間到宮廷,再返民間的過程,這一過程與宮廷內(nèi)外的戲曲互動息息相關(guān),停云室曲家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媒介。
余論
由于清初宮廷戲曲檔案留存不多,所以清初宮廷戲曲的許多相關(guān)問題較難確證。停云室曲家雙重身份的確定,一定意義上有助于戲曲史研究的深化。例如,關(guān)于清代南府和宮廷教習的設(shè)置時間,學界多征引焦循《劇說》所引《菊莊新話》的記載,認為宮廷戲曲教習設(shè)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自康熙南巡至蘇州時挑選藝人入宮。前文引及,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月二十日“郎中費郎古等為宮廷用項開支銀兩的題本”中提到:“糊南府(音譯)所用戲臺架子……給教習王正祥絨纓子涼帽一,此項銀八錢。”朱家溍提出:“這是至今見到有確切時間的最早的南府的出現(xiàn)。”[26]的確。這也是提及宮廷戲曲教習最早的記錄。需要注意的是,這一記錄并不代表著南府以及宮廷教習最早出現(xiàn)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停云室出版作品的時間集中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此之前王正祥、儲國珍等人應(yīng)已久處北京。同時,儲國珍之孫出生于康熙丙寅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這一時期的儲氏家族早已在北京具有一定的交游范圍和生活背景,可見儲國珍進入北京并成為清宮戲曲教習的時間也應(yīng)在此之前。這也可以佐證,將《封神榜》的創(chuàng)作時間上限推定為康熙十五年(1676)有其合理性。
清宮檔案記錄了數(shù)量眾多的戲曲教習和民籍藝人名單,這些民間藝人較少撰述,也不為正史所載,對這一群體進行深入研究的難度較大。本文通過文獻考證確定了王正祥、儲國珍的宮廷教習身份,進而發(fā)現(xiàn)了一批由宮廷教習組織創(chuàng)作的劇本、曲譜等作品。承應(yīng)于宮廷的王正祥、儲國珍等宮廷教習,通過劇本創(chuàng)作影響民間戲曲的演出形式,通過一系列理論著作,將宮廷戲曲的體制規(guī)范傳入民間,對民間戲曲聲腔、格律的上升發(fā)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停云室曲家及作品,清晰地展現(xiàn)了清初宮廷戲曲與民間戲曲互動發(fā)展的脈絡(lu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研究視野。宮廷檔案中眾多民籍教習與藝人的信息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宮廷戲曲相關(guān)問題的研究尚有細化的空間和可能。
注 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戲曲稿抄本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2&ZD267)。
[1]《恩賞日記檔》,載中國國家圖書館編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昇平署檔案集成》(第1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34頁。
[2]瞿冕良編著:《中國古籍版刻辭典(增訂本)》,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13頁。
[3]大連市圖書館文獻研究室、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譯編:《大連市圖書館藏清代內(nèi)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職司銓選 獎懲 宮廷用度 宮苑 進貢》,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205、第217、第229頁。
[4]儲鳳林等:《宜興南臧儲氏分支譜》卷二,清光緒十九年(1893)永綏堂活字印本,南京圖書館藏,索書號:GJ/EB/2004998。
[5]莊清逸:《南府之沿革》,《上海畫報》1932年第835期。
[6]王正祥等:《宗北歸音》,《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7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頁。
[7]儲鳳林等:《宜興南臧儲氏分支譜》卷二。
[8]孟子著,楊伯峻、楊逢彬注釋:《孟子》,岳麓書社2000年版,第81頁。
[9]周貽白:《中國戲劇史長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581頁。
[10]吳曉鈴:《〈古本戲曲叢刊〉九集序稿》,《吳曉鈴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頁。
[11]停云室編:《封神榜》,載《俗文學叢刊》(第58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73-374頁。
[12]停云室編:《封神榜》,載《俗文學叢刊》,第368頁。
[13]停云室編:《封神榜》,第372頁、第375頁。
[14]參見楊晶蕾《〈封神天榜〉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2017年,第11-12頁。
[15]停云室編:《封神榜》,第461頁。
[16]參見王正祥等《十二律京腔譜》,《善本戲曲叢刊》(第3輯),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版,第311-312頁。
[17]周貽白:《中國戲劇史長編》,第489頁。
[18]昆崗等修,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〇三九,《續(xù)修四庫全書》(第81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5頁。
[19]李光庭:《鄉(xiāng)言解頤》,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4頁。
[20]周祥鈺等:《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載《善本戲曲叢刊》(第6輯),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版,第31-32頁。
[21]參見拙文《論〈宗北歸音〉的昆腔北曲格律譜性質(zhì)及其曲學意義》,《南大戲劇論叢》2023年第2期。
[22]吳梅:《十二律昆腔譜跋》,載王正祥編纂《新定十二律昆腔譜》,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23]愛新覺羅·玄燁:《圣祖諭旨》,載故宮博物院掌故部編《掌故叢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51頁。
[24]王正祥等:《十二律京腔譜》,第27-28頁。
[25]夏仁虎:《枝巢四述 舊京瑣記》,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頁。
[26]朱家溍、丁汝芹:《清代內(nèi)廷演劇始末考》,第13頁。
本文原載于《中華戲曲》第73輯,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24年版。引用時請以原刊為準。
— END —
【2025年推送文章】
田曉婧:《長生殿》《桃花扇》經(jīng)典化歷程中的清代文人評點探賾
潘培忠、周紅霞:近代報刊與《病玉緣傳奇》的出版?zhèn)鞑?/a>
田仲一成:廣東鄉(xiāng)村里的目連破獄儀式——八門功德
楊少偉:碩園生平家世新考——兼談《碩園刪定牡丹亭》的初印時間
劉于鋒、黃瑩:李伯元與《玉鉤痕傳奇》的征題創(chuàng)作
盛書琪:論近代曲藝批評的轉(zhuǎn)型、特征及意義——以近代報刊為中心
杜翹楚:徐家禮及其《蟄園曲》考補——兼論晚清曲社成員的戲曲創(chuàng)作特征
王珮璠:新編昆劇舞臺敘事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
歡迎關(guān)注中華戲劇學刊聯(lián)盟刊物公眾號
中央戲劇學院學報
《戲劇》
上海戲劇學院學報
《戲劇藝術(shù)》
《戲曲研究》
《戲曲與俗文學研究》
《南大戲劇論叢》
中國戲曲學院學報
《戲曲藝術(shù)》
《中華戲曲》
掃碼關(guān)注我們
微信號|
zhonghuaxiqu1986
投稿郵箱|
編校 || 董 ? 鑫
初審 || 公蒗蒗復審 ||?郝成文
終審 || 呂文麗

![]()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查看免費推送
- 南京招標網(wǎng)
- 無錫招標網(wǎng)
- 鎮(zhèn)江招標網(wǎng)
- 蘇州招標網(wǎng)
- 南通招標網(wǎng)
- 揚州招標網(wǎng)
- 鹽城招標網(wǎng)
- 徐州招標網(wǎng)
- 淮安招標網(wǎng)
- 連云港招標網(wǎng)
- 常州招標網(wǎng)
- 泰州招標網(wǎng)
- 宿遷招標網(wǎng)
- 建湖縣招投標
- 湖北|網(wǎng)上采購招標平臺
- 高坪區(qū)財政局
- 陜西省及政府采購與招標網(wǎng)
- 宣城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鎮(zhèn)江市丹徒區(qū)
- 廣南縣招投標中心
- 政府采購招標方式
- 廣東建設(shè)網(wǎng)
- 沙洋縣招投標中心
- 秦都區(qū)人民政府
- 天津|陽光采購平臺招標信息
- 采購洗碗機
- 溫州裝修招標
- 海滄區(qū)人民政府
- 上海地鐵招投標告示
- 普蘭店政府招標網(wǎng)
- 凌源市政府采購網(wǎng)
- 上海交易采購中心
- 信息招標網(wǎng)
- 山東省|招投標公共信息服務(wù)平臺
- 河北張家口下花園區(qū)應(yīng)急管理局
- 昌平招標網(wǎng)
- 建工集團招標
- 晉城招標工程
- 彬州市人民政府
- 臨沭縣政務(wù)服務(wù)中心
- 防暴頭盔
- 寧波招投標余姚分中心
- 中國石油招標平臺
- 高州市財政局
- 撫順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
- 新干縣財政局
- 塔河縣人民政府
- 國信招投標信息網(wǎng)
- 湖北|省政府采購招標平臺
- 貴州省招標有限公司
- 高速公路招標公告
- 白酒物流配送招標
- 樂山市財政局
- 廣陵區(qū)人民政府
- 印刷政府采購
- 電源招標采購網(wǎng)
- 膠州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廈門市思明區(qū)
- 充電樁工程招標流程
- 南陽市招標中心
- 什邡市財政局
- 江蘇公共資源
- 干部培訓項目招標
- 沈河區(qū)人民政府
- 郫都區(qū)人民政府
- 競爭性招標采購5G
- 張北縣政府公開信息
- 安徽大學
- 清華大學|招標采購中心
- 宜都市招投標中心
- 皖西衛(wèi)生職業(yè)學院
- 周口招標代理
- 南京仙林大學城
- 克東縣人民政府
- 哈密政府采購
- 河北省供電公司招標公告
- 昌樂縣招投標中心
- 威海市環(huán)翠區(qū)
- 國鐵采購平臺
- 濱海縣衛(wèi)生局招標網(wǎng)
- 湖南招標信息網(wǎng)
- 鄭州招投標人員招聘
- 沭陽招標采購網(wǎng)
- 海南建設(shè)交易網(wǎng)
- 寧夏建設(shè)網(wǎng)
- 鋼筋切斷機招標采購
- 平遙縣電力交易中心
- 天津招標投標公共服務(wù)平臺
- 河北華電招標網(wǎng)
- 湖北招標與采購網(wǎng)
- 清江浦區(qū)人民政府
- 關(guān)于醫(yī)院政府采購招標流程
- 泉州招標代理
-
 聯(lián)系客服
聯(lián)系客服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信息發(fā)布
信息發(fā)布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招標訂閱
招標訂閱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商機挖掘
商機挖掘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數(shù)據(jù)定制
數(shù)據(jù)定制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標書代寫
標書代寫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資質(zhì)辦理
資質(zhì)辦理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投標咨詢
投標咨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證書查詢
證書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綠色報告查詢
綠色報告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