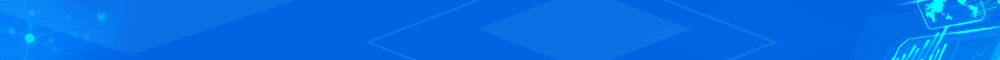達(dá)吾力江·葉爾哈力克 任冠 | 2024年新疆奇臺(tái)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工作主要收獲
所屬地區(qū):新疆 - 昌吉 發(fā)布日期:2025-05-07發(fā)布地址: 新疆
來(lái)源:《西域研究》2025年第2期
2024年新疆奇臺(tái)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工作主要收獲[1]
達(dá)吾力江·葉爾哈力克 任冠
2024年唐朝墩古城遺址的考古發(fā)掘,主要清理了城址中心佛寺的周邊遺址,在佛寺東側(cè)清理出佛寺山門以及其他房屋建筑,南側(cè)清理出數(shù)間房屋建筑,并在其中發(fā)現(xiàn)佛教塑像、經(jīng)卷殘片、織物等遺物。佛寺遺址東側(cè)、南側(cè)各發(fā)現(xiàn)一條東西向道路,其中一條對(duì)應(yīng)佛寺山門并延伸至城址東部,初步判斷其為城內(nèi)東西向主干街道。城址東部及佛寺南部發(fā)現(xiàn)有三處性質(zhì)不同的房址,為探索城址功能分區(qū)與不同區(qū)域建筑性質(zhì)提供了新的線索。
唐朝墩古城遺址位于新疆昌吉奇臺(tái)縣東北部,在天山北麓沖積平原的綠洲廊道上,是絲綢之路北道東段的重要交通樞紐,也是庭州治下一處重要的軍政建置。據(jù)考,唐朝墩古城始建于唐貞觀十四年(640)前后,初為蒲類縣縣治所在,后歷經(jīng)高昌回鶻、西遼及元等歷史時(shí)期沿用,直至14世紀(jì)中葉逐漸廢棄。自2018年起,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開展唐朝墩古城遺址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工作,發(fā)掘了包括唐代院落遺址、高昌回鶻時(shí)期浴場(chǎng)、唐至元時(shí)期佛寺遺址和景教寺院遺址等多處重要考古遺存,研究了城址布局與建筑形制,分析了年代序列與宗教遺存性質(zhì),為深入認(rèn)識(shí)唐朝墩在內(nèi)的新疆唐至元時(shí)期城市的歷史變遷與文化內(nèi)涵提供了豐富的實(shí)物資料。
2024年唐朝墩的考古工作主要包括三個(gè)方面,一是清理佛寺遺址東側(cè)及南側(cè)區(qū)域,確定佛寺范圍及建筑布局;二是發(fā)掘城址中部、東部三處建筑基址,確定其結(jié)構(gòu)與性質(zhì);三是整理2018~2023年考古發(fā)掘資料,開展出土壁畫與經(jīng)卷的加固保護(hù)項(xiàng)目。
一 考古發(fā)掘與收獲
2024年度唐朝墩遺址批準(zhǔn)發(fā)掘面積為1000平方米,城址中部、南部及東部分設(shè)3個(gè)發(fā)掘區(qū)(圖1),共清理房址12處,墻體11處,灶址9處,灰坑121個(gè),灰溝2條,水井1口,土臺(tái)3處,還發(fā)現(xiàn)道路2條、窯址1座。
圖1 唐朝墩古城遺址發(fā)掘區(qū)示意圖
(淡藍(lán)色區(qū)域?yàn)?024年發(fā)掘區(qū))
(一)佛寺遺址
唐朝墩城址中央高臺(tái)為一處佛教寺院遺址,經(jīng)發(fā)掘確定其為唐代始建,沿用至高昌回鶻時(shí)期和元時(shí)期,出土佛造像和蓮花紋瓦當(dāng)?shù)冗z物,并在佛殿佛臺(tái)壁面發(fā)現(xiàn)彩繪壁畫(圖2)。[2]2024年的考古工作重點(diǎn)發(fā)掘佛寺遺址庭院東部及南部區(qū)域,清理出多處建筑基址,并在佛寺遺址外圍東側(cè)、南側(cè)各發(fā)現(xiàn)一條東西向道路。
圖2 2020年佛寺遺址出土遺物與壁畫
1.佛寺東側(cè)建筑
佛寺東側(cè)清理出上下疊壓的兩期建筑,分別為F23和F27,兩者結(jié)構(gòu)較為相似,推測(cè)為佛寺不同時(shí)期的建筑。該建筑在元時(shí)期寺院毀壞后被重新改建利用。
佛寺東側(cè)建筑遺址F23平面呈長(zhǎng)方形,墻體使用多層土坯壘砌而成,地面鋪設(shè)多層土坯(圖3),部分墻體涂抹白灰并殘留彩繪痕跡。其主體結(jié)構(gòu)為F23-1,整體呈東西向“凸”字形,南北約7米,東西約10米,東墻中部開設(shè)門道。門道以東發(fā)現(xiàn)一條東西向道路L6,最寬處近10米,自上至下至少包含三層路面。
圖3 佛寺遺址發(fā)掘區(qū)示意圖
F23-1房?jī)?nèi)地面通鋪土坯,根據(jù)鋪設(shè)方式不同可分為四個(gè)區(qū)域。南部和北部土坯緊鄰南北墻體,其東側(cè)對(duì)稱分布兩個(gè)半圓形石質(zhì)柱礎(chǔ),直徑約45厘米。西部土坯存四層土坯,其東北部發(fā)現(xiàn)一圓形柱礎(chǔ)石,直徑約為45厘米。東部土坯結(jié)構(gòu)上下共鋪設(shè)三層。
F23-2和F23-3位于F23-1北部,其中F23-2南北近3米,東西約10米,西墻有門道,寬約1.75米。靠近門道兩側(cè)有三處柱洞,呈南北相對(duì)分布,其中殘存燒毀木柱。F23-3位于F23-2北部,其西墻中部門道寬約0.7米,房址中出土壁畫殘塊,其上可見紅、藍(lán)色彩和黑色線條圖案。
另有一組建筑F27疊壓于F23下,墻體以土坯壘砌。其中F27-1整體呈長(zhǎng)方形,長(zhǎng)約11.2米,寬約9.8米,其東墻設(shè)置門道,長(zhǎng)約2.15米,寬約1米,門道南側(cè)東墻外壁面抹白灰,其南部有四處柱礎(chǔ)石。上層F23西墻外側(cè)發(fā)現(xiàn)的東西向道路亦見于F27西側(cè),路面寬約4.5米。F27-2、F27-3與上層F23-2、F23-3房址形制較為相似,兩處房址內(nèi)均發(fā)現(xiàn)有壁畫殘塊,可見紅、藍(lán)色彩及黑色線條。F27-2發(fā)現(xiàn)有炭化木構(gòu)件,呈圓柱形,直徑約6厘米,外側(cè)刻有多層花瓣形裝飾,或?yàn)榻ㄖ?gòu)件。
根據(jù)層位關(guān)系和出土遺物,F(xiàn)23年代約為西遼至元時(shí)期,F(xiàn)27年代約為高昌回鶻中期至晚期,二者為佛寺不同時(shí)期的山門遺址,F(xiàn)23-1和F27-1為門殿所在,北側(cè)房址可能為不同功能的佛殿。
2.佛寺南側(cè)建筑
佛寺前院南側(cè)清理出多組房址,其中F24緊鄰佛寺,整體呈“T”形,內(nèi)部清理出5個(gè)房間。
F24-1平面呈長(zhǎng)方形,墻體多使用土坯壘砌。其中西墻保存較好,長(zhǎng)約7.75米,寬約0.75米,北墻長(zhǎng)約5.4米,寬約0.6米。東墻向北側(cè)延伸,與F24-3南墻相接,長(zhǎng)約8.75米,寬約1.5米。F24-1中部有東西向和南北向兩段殘存墻體形成拐角,或用于分隔房間的西北區(qū)域。F24-2位于F24-1東北,東墻長(zhǎng)約5.75米,寬約2米,東墻內(nèi)側(cè)底部發(fā)現(xiàn)兩處圓形柱洞遺存。F24-3南北約3.7米,東西約7.7米,房?jī)?nèi)發(fā)現(xiàn)有四處柱洞遺跡。F24-4位于F24-3西側(cè),平面為東西向長(zhǎng)方形,南北約5米,東西約10米,墻體采用土坯壘砌。F24-4房?jī)?nèi)堆積由上至下可分為三層,其中①層出土大量泥塑殘塊、炭化紙張、織物,并發(fā)現(xiàn)少量帶有金箔的木制品與經(jīng)卷殘片,此外還出土一件泥塑頭像(F24-4①:5)以及大量手指造型的泥塑,或?yàn)榉鹣駳垑K。F245僅清理出北墻與東墻,其中北墻長(zhǎng)約10.5米,寬約0.75米,東墻長(zhǎng)約2.6米,寬約2米。F31位于建筑群南部,被晚期灰坑破壞嚴(yán)重,僅見西、北、南三處墻體。
根據(jù)地層關(guān)系可推斷F24-1、F24-2、F24-3、F24-4①以及F24-5年代為西遼至元時(shí)期,F(xiàn)24-4②年代為高昌回鶻中晚期,F(xiàn)24-4③年代為高昌回鶻早期。根據(jù)房址結(jié)構(gòu)與出土遺物,推測(cè)F24應(yīng)為佛寺南側(cè)多組佛殿及僧房遺址。
(二)道路遺跡
1.道路L6
城址東部發(fā)掘區(qū)發(fā)現(xiàn)一條東西貫穿IIT2327、IIT2329、IIT2331三個(gè)探方的道路L6,寬約3.9~4.6米,殘存厚度約1.22米,包括5層路面,使用時(shí)間較長(zhǎng)。
探方IIT2331內(nèi)道路路面發(fā)現(xiàn)大量陶片堆積,另在探方IIT2329與探方IIT2331路面南側(cè)、北側(cè)各發(fā)現(xiàn)兩條長(zhǎng)約3米的東西向條狀堆積,由經(jīng)過(guò)挑選、大小相近的圓角方形石塊組成,推測(cè)該遺跡與街道排水系統(tǒng)有關(guān)。
根據(jù)地層推斷道路L6起建于唐代,沿用至元時(shí)期。就唐朝墩古城整體布局而言,L6向東對(duì)應(yīng)城址東門,向西直通佛寺山門,最寬處可達(dá)10米,可能為城內(nèi)一條東西向主干道。
2.道路L5
道路L5位于佛寺南側(cè),為一條東西向道路,最寬處達(dá)6.25米,殘存厚度約1.4米,同樣包含多層路面。根據(jù)地層推斷L5始建于唐代,至元時(shí)期廢棄,晚期路面被房屋侵占疊壓。
(三)其他房址
1.佛寺南側(cè)房址
探方IIT1412中L5南側(cè)清理出F29、F30等多處房址。F29平面呈長(zhǎng)方形,北墻長(zhǎng)約10米,西墻長(zhǎng)約1.5米,東墻與北墻垂直,長(zhǎng)約8.5米,南側(cè)被破壞。根據(jù)地層關(guān)系可推斷F29為高昌回鶻晚期房址。
F29房北墻西部被窯址Y1打破,Y1平面呈馬蹄形,從南至北由火膛、窯床、煙道三部分組成,窯室東北側(cè)及南側(cè)被晚期灰坑打破,操作間、窯門未存。窯室南部為火膛,平面呈梯形,南北長(zhǎng)約1.24米,東西寬約0.7~1.56米,深約1米,火膛四壁及底部均有堅(jiān)硬燒結(jié)面。窯床平面呈不規(guī)則方形,四壁由土坯壘砌,南北約2.4米,東西寬約2.74米,窯床底部有燒結(jié)面。窯床北側(cè)發(fā)現(xiàn)兩條煙道,北緣呈弧形,寬度為0.4米,殘高0.35米。
F30平面呈方形,北墻分為上下兩層,長(zhǎng)約10米,寬約1.3~1.4米,南墻寬約0.7米,南北墻相距約4.15米。東墻中部被H1079、H1081打破,推測(cè)為門道位置。西墻寬約0.7米,被H1096、H1105打破。房?jī)?nèi)出土較多鐵器,并有銅帶扣、陶紡輪、穿孔石器等遺物。根據(jù)地層推測(cè)F30始建于唐代,至高昌回鶻時(shí)期在其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修筑并沿用。
2.城址東部房址
城址東部在探方IIT2329、IIT2331清理出多處房址,其中F26、F32為相連兩個(gè)房屋建筑。F26僅清理出西墻和南墻,墻體堆筑而成,西墻殘存長(zhǎng)度約5.15米,寬約1.2米;南墻殘長(zhǎng)2.5米,寬1.2米。F26房址內(nèi)出土彩繪泥塑、壁畫殘塊,壁畫殘塊可見紅、藍(lán)、黑三色,房?jī)?nèi)還發(fā)現(xiàn)陶俑頭像(IIT2331④:2)。房?jī)?nèi)出土陶器多為素面夾細(xì)砂紅陶,表面有火燒痕跡,根據(jù)地層推測(cè)F26為唐代建筑。
F32東墻即F26西墻,F(xiàn)32南墻長(zhǎng)約1.35米,寬約1.16米。墻體堆筑而成。房?jī)?nèi)西北角發(fā)現(xiàn)一生土起建的夯筑土臺(tái)(T7),平面近弧角方形,長(zhǎng)度3米,寬3.25米,高度2.1米,剖面可見明顯夯層,包含有較多膠泥塊和小顆粒石塊。高臺(tái)四周使用土坯圍砌。F32應(yīng)與F26為同一時(shí)期,推測(cè)為唐代建筑。
F22位于T2329,平面呈“E”形,整體南北向分布,東西寬約2米,南北長(zhǎng)約3.8米,主要由三道東西向墻體和一道南北向墻體組成,中部墻體將房間分為南北兩個(gè)部分,根據(jù)地層推測(cè)F22年代為高昌回鶻中晚期。
3.城址東部北側(cè)房址
城址東部北側(cè)發(fā)掘區(qū)IIT3030、IIT3230清理出房址F21,平面呈長(zhǎng)方形,整體南北向分布,可分為三個(gè)房間。
F21-1僅東墻保存較好,墻體上層為土坯壘砌,下層垛泥堆筑,長(zhǎng)約10米,北墻殘長(zhǎng)5.2米,西墻整體被灰坑打破,南墻東部保存有寬約2米門道。房間中部有一土臺(tái),清理出三條南北向煙道。F21-2東墻長(zhǎng)約2米,北墻長(zhǎng)約7.8米。F21-3中部偏北發(fā)現(xiàn)一處土臺(tái),內(nèi)部保存三條南北向煙道。F21東、西墻墻體外部以土坯壘砌,中央有寬約20厘米的條狀灰燼堆積,或?yàn)榛饓煹澜Y(jié)構(gòu)。
二 出土遺物
2024年度發(fā)掘出土遺物小件共計(jì)358件(組),包括陶器、瓷器、銅器、鐵器、石器、骨角器、玻璃(琉璃)器、貝類、木器、泥塑、紙張和織物等。其中佛寺遺址出土的泥塑、經(jīng)卷、織物和樹皮等文物,已完成初步加固和修復(fù)工作。
1.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以陶器為主,器型包括罐、甕、壺、缽、盆、盞等,多為盛裝器或炊器(圖4),多見附加堆紋和水波紋,另有少量飾特殊刻劃圖像。如陶壺H1073:3和陶罐H1093:5(圖5),后者器身上腹刻劃順時(shí)針萬(wàn)字符。部分陶器殘片可見盤角羊頭浮雕圖案和聯(lián)珠紋圖案,部分陶器通體保存火燒痕跡,或具有特殊用途。
圖4(左圖) H1037出土陶器組合圖
圖5(右圖) 刻劃符號(hào)陶器H1073:3(左)和H1093:5(右)
除陶器外,還發(fā)現(xiàn)有砂玻器和瓷器殘片,其中砂玻器(H1088:1)通高15.7厘米,胎體夾細(xì)砂和石英,外施青綠色釉,器身腹部呈瓜楞狀(圖6)。另有兩片可拼對(duì)的黑地白花瓷片(H1062:2),裝飾有花卉圖案,內(nèi)壁施黑褐色釉。
圖6 砂玻器H1088:1
2.生產(chǎn)工具
生產(chǎn)工具以陶紡輪數(shù)量最多,此外常見石磨盤、石鋤等石器,其中有一件較為完整的陶犁(F23-1:1),殘長(zhǎng)18厘米,最寬處12.1厘米。器體為夾粗砂紅陶,外施黃褐色陶衣,器身呈等腰三角形,背部拱起,殘斷處中部有一孔洞,內(nèi)部有殘碎骨頭。
3.飾品
飾品以珠飾為主,包括石質(zhì)、瑪瑙、琉璃、貝殼、綠松石等材質(zhì),多有穿孔。除珠飾外,還出土有銅帶扣、銅環(huán)、銅鈴等金屬飾件。
4.塑像
佛寺南側(cè)房址F24-4內(nèi)出土大量塑像殘塊,其中F24-4①:5為泥塑頭像,殘長(zhǎng)9.23厘米,殘寬7.75厘米,表面呈灰褐色,殘留面部右側(cè)鼻、嘴、臉頰、下巴等部位,面部形態(tài)豐滿(圖7)。
圖7 泥塑頭像(F24-4①:5)
此外,還出土數(shù)十件泥塑手指,最長(zhǎng)約9厘米,最短約2.5厘米,殘寬約0.9~2.1厘米,厚約1~2厘米,部分內(nèi)部殘存銹蝕的鐵質(zhì)支撐芯或孔洞,手指粗細(xì)不同,姿勢(shì)各異,可分辨左右不同手指部位、以及手指伸直或彎曲等不同形態(tài)。該房址內(nèi)還出土植物、動(dòng)物及環(huán)狀泥塑,推測(cè)均為佛教塑像殘塊(圖8)。
圖8 塑像殘塊(F24-4①:9)
城址東部房址F26內(nèi)出土一件陶俑頭像(T2331④:2),夾細(xì)砂紅陶,殘高8.5厘米。人物雙眼圓睜,頭部似有對(duì)翼頭冠,臉頰兩側(cè)有“8”字形耳飾(圖9)。
圖9 陶俑頭像(T2331④:2)
5.經(jīng)卷
佛寺南側(cè)房址F24-4內(nèi)出土多件被燒毀經(jīng)卷殘片,部分為殘留木質(zhì)圓柱形軸芯的卷軸。其中較完整的一件F24-4①:27殘長(zhǎng)8.5厘米,殘寬2.5厘米,其外側(cè)殘留多層紙張殘片,呈卷軸狀,經(jīng)卷內(nèi)側(cè)為正面,書寫漢文,外側(cè)為背面,書寫回鶻文(圖10)。漢文中可識(shí)讀“人有一涅”“眾生深”等文字(圖11)。另有部分殘片(F24-4①:7)雙面均可識(shí)別漢字,字體風(fēng)格與F24-4①:27也有所不同(圖12)。
6.壁畫
本年度開展了唐朝墩遺址出土壁畫保護(hù)與修復(fù)項(xiàng)目。修復(fù)過(guò)程中在景教寺院IVT0937②:1中清理出數(shù)行墨書文字,經(jīng)北京大學(xué)林麗娟博士釋讀為敘利亞文,可識(shí)別包括“主”“信仰”“罪”等詞(圖13)。
圖13 IVT0937②:1殘存敘利亞文
三 初步認(rèn)識(shí)
2024年唐朝墩古城遺址的考古工作重點(diǎn)關(guān)注佛寺東側(cè)及南側(cè)建筑群,清理出建筑基址及多處房址,進(jìn)一步明確了佛寺遺址的布局結(jié)構(gòu)和歷史沿革。推測(cè)佛寺庭院東側(cè)建筑是佛寺山門,為東西向凸字形門殿結(jié)構(gòu),地面鋪設(shè)多層土坯,保留有門道及石質(zhì)柱礎(chǔ);佛寺山門北側(cè)與庭院南側(cè)的多組房址,推測(cè)為配殿和僧房。通過(guò)對(duì)佛寺遺址的進(jìn)一步發(fā)掘,確認(rèn)佛寺遺址整體東西約66米,南北約42米,占地面積近2800平方米。根據(jù)地層堆積與出土遺物,判斷寺院最初建于唐代,高昌回鶻、元時(shí)期歷經(jīng)毀壞與重修,與城址及景教寺院情況相似。
佛寺南側(cè)房址F24-4中發(fā)現(xiàn)大量炭化紙張,并出土木質(zhì)卷軸軸芯,部分殘紙可識(shí)別出漢文與回鶻文。F24-4①:27根據(jù)漢文內(nèi)容判斷為《大般涅槃經(jīng)》,測(cè)年結(jié)果顯示紙張年代約為唐代中期(公元8~9世紀(jì))[3],背面的回鶻文可能為高昌回鶻時(shí)期增補(bǔ)的注解或論疏。該批紙質(zhì)佛經(jīng)為天山北麓地區(qū)首次發(fā)現(xiàn),為研究佛教在西域的傳播提供了重要資料。
佛寺以外東側(cè)、南側(cè)各發(fā)現(xiàn)一條東西向道路,其中L6連通佛寺山門與城址東部,推斷為城內(nèi)一條東西向主干道。L5位于佛寺遺址南部,為另一條東西向道路。根據(jù)地層關(guān)系與遺跡現(xiàn)象,兩條道路均始建于唐代,至元時(shí)期廢棄,其間經(jīng)過(guò)多次鋪設(shè)。道路遺跡的發(fā)現(xiàn)為考察城內(nèi)街道系統(tǒng)與功能分區(qū)提供了重要依據(jù)。
除佛寺遺址外,本年度的發(fā)掘工作還清理出三片性質(zhì)不同的房址區(qū)。佛寺南側(cè)L5以南發(fā)現(xiàn)F29、F30等房址,清理出借助F29北墻建造的窯址Y1;東部L6北側(cè)清理出院落遺址F26,出土了包括陶俑頭像、彩繪泥塑、壁畫殘塊、帶刻劃符號(hào)的陶器在內(nèi)的大量遺物,并發(fā)現(xiàn)以生土夯筑的土臺(tái)和大量燒火痕跡。結(jié)合測(cè)年數(shù)據(jù),該房址為唐代建筑,推測(cè)其性質(zhì)較為特殊,可能為城內(nèi)除佛教、景教外另一處具有宗教性質(zhì)的遺址。城址東部北側(cè)清理出南北向房址F21,房址內(nèi)壘砌土炕結(jié)構(gòu),墻體內(nèi)發(fā)現(xiàn)有煙道結(jié)構(gòu),推測(cè)是民居或具有驛館性質(zhì)的建筑。上述房址的發(fā)掘?yàn)樘接懗侵氛w布局與文化內(nèi)涵提供了新的線索。
近年來(lái),唐朝墩古城遺址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取得了顯著進(jìn)展,城市文化面貌愈加清晰,考古成果不僅為新疆地區(qū)首次發(fā)現(xiàn),更引起了國(guó)際學(xué)界關(guān)注,成為絲綢之路城市考古與宗教領(lǐng)域的研究熱點(diǎn)。唐朝墩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展現(xiàn)了唐至元代天山北麓地區(qū)多民族和諧共生、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交融的歷史圖景,凸顯了天山廊道作為商貿(mào)交流、宗教傳播、不同群體間交往交流交融通道的重要作用,為探究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交流、多民族大一統(tǒng)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啟示。
?注釋
[1] 本文為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青年項(xiàng)目“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資料的整理與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1CKG016)的階段性成果;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青年項(xiàng)目“漢晉西域城址與軍政建置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2CKG017)的階段性成果;“考古中國(guó)——新疆考古項(xiàng)目——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發(fā)掘”的階段性成果。
[2] 任冠,魏堅(jiān):《二〇一八~二〇二〇年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發(fā)掘的主要收獲》,《文物天地》2021年第7期,第120~121頁(yè);魏堅(jiān),鄭玉:《中西文化的交匯——唐朝墩古城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的啟示》,《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2022年第4期,第14~15頁(yè);王曉丹,任冠:《唐朝墩佛寺遺址反映城市興衰與絲路交流》,《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23年4月6日第A04版。
[3] 碳十四數(shù)據(jù)由蘭州大學(xué)西部環(huán)境教育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碳十四實(shí)驗(yàn)室檢測(cè)。
(作者單位: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
編排:王常興
審校:王文洲
審核:陳 霞
微信:西域研究

![]()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hào)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hào)
免費(fèi)查看免費(fèi)推送
- 塔城招標(biāo)網(wǎng)
- 哈密招標(biāo)網(wǎng)
- 和田招標(biāo)網(wǎng)
- 阿勒泰招標(biāo)網(wǎng)
- 克孜勒蘇招標(biāo)網(wǎng)
- 博爾塔拉招標(biāo)網(wǎng)
- 克拉瑪依招標(biāo)網(wǎng)
- 烏魯木齊招標(biāo)網(wǎng)
- 石河子招標(biāo)網(wǎng)
- 昌吉招標(biāo)網(wǎng)
- 吐魯番招標(biāo)網(wǎng)
- 巴音郭楞招標(biāo)網(wǎng)
- 阿克蘇招標(biāo)網(wǎng)
- 喀什招標(biāo)網(wǎng)
- 伊犁招標(biāo)網(wǎng)
- 阿拉爾招標(biāo)網(wǎng)
- 圖木舒克招標(biāo)網(wǎng)
- 五家渠招標(biāo)網(wǎng)
- 北屯招標(biāo)網(wǎng)
- 鐵門關(guān)招標(biāo)網(wǎng)
- 雙河招標(biāo)網(wǎng)
- 可克達(dá)拉招標(biāo)網(wǎng)
- 昆玉招標(biāo)網(wǎng)
- 鞏義市財(cái)政局
- 茨溝鎮(zhèn)茨溝初級(jí)中學(xué)
- 朔城區(qū)政務(wù)服務(wù)中心
- 蘇州工程造價(jià)信息
- 遂溪縣融媒體中心
- 邢臺(tái)中煤旭陽(yáng)招標(biāo)網(wǎng)
- 銅鼓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宣城市招投標(biāo)信息網(wǎng)
- 十堰市鄖西縣
- 東莞市招標(biāo)
- 代理招標(biāo)合同
- 蘇州市氣象局
- 河南政府采購(gòu)招標(biāo)綜合網(wǎng)
- 魯泰|控股招投標(biāo)平臺(tái)
- 英德網(wǎng)上中介超市
- 浙江省氣象信息網(wǎng)絡(luò)中心
- 浙江省+電力|采購(gòu)中心平臺(tái)
- 宜賓市政府采購(gòu)網(wǎng)
- 眉縣政府信息公開網(wǎng)
- 國(guó)義招標(biāo)采購(gòu)平臺(tái)
- 吉林工業(yè)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 中堂朝陽(yáng)幼兒園招標(biāo)信息
- 萊蕪分公司電子采購(gòu)平臺(tái)
- 下城區(qū)教育局
- 南通市
- 劇院招標(biāo)
- 鐵建云商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
- 扶綏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金昌耐磨地坪涂料采購(gòu)
- 四川建設(shè)交易網(wǎng)
- 采購(gòu)招標(biāo)方式有幾種
- 沭陽(yáng)縣教育局
- 崇禮縣人民政府網(wǎng)
- 長(zhǎng)春公共資源
- 發(fā)電機(jī)招標(biāo)
- 中央政府采購(gòu)平臺(tái)
- 英德市招投標(biāo)中心
- 肥西縣謝塘小學(xué)
- 山東交通職業(yè)學(xué)院
- 歷城區(qū)人民政府
- 朝陽(yáng)市電力交易中心
- 扶貧辦
- 昌吉招標(biāo)工程
- 硚口區(qū)教育局
- 會(huì)昌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遼寧政務(wù)服務(wù)網(wǎng)
- 噴漿機(jī)招標(biāo)采購(gòu)
- 陜西采購(gòu)與招標(biāo)公共平臺(tái)
- 富陽(yáng)招標(biāo)信息網(wǎng)
- 臺(tái)州市政務(wù)服務(wù)中心
- 北京市延慶區(qū)人民政府
- 藥品集中招標(biāo)采購(gòu)模式
- 云南省建設(shè)招標(biāo)
- 壽光政府采購(gòu)招標(biāo)網(wǎng)
- 壓裂招標(biāo)
- 正定縣人民政府網(wǎng)
- 海南省建設(shè)招標(biāo)
- 象山縣政務(wù)服務(wù)中心
- 電子屏采購(gòu)
- 政府采購(gòu)和公開招標(biāo)區(qū)別
- 中國(guó)航發(fā)網(wǎng)上商城
- 溫州市龍灣區(qū)
- 西安市招標(biāo)中心
- 陜西省招標(biāo)信息公示網(wǎng)
- 寧波市江北區(qū)
- 阜外醫(yī)院招標(biāo)
- 雙遼市人民政府網(wǎng)
- 麗水市招投標(biāo)信息網(wǎng)
- 廣平縣政務(wù)服務(wù)中心
- 岳陽(yáng)政府采購(gòu)
- 中遠(yuǎn)采購(gòu)平臺(tái)
- 三臺(tái)縣招標(biāo)
- 吉林省建設(shè)項(xiàng)目采購(gòu)信息網(wǎng)
- 環(huán)保局
- 廣州市國(guó)家稅務(wù)局
- 河北北方學(xué)院
- 上海政采中心
- 首都醫(yī)科大學(xué)
- 定興縣人民政府
- 中國(guó)招標(biāo)采購(gòu)公共服務(wù)
-
 聯(lián)系客服
聯(lián)系客服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信息發(fā)布
信息發(fā)布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招標(biāo)訂閱
招標(biāo)訂閱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商機(jī)挖掘
商機(jī)挖掘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數(shù)據(jù)定制
數(shù)據(jù)定制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標(biāo)書代寫
標(biāo)書代寫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資質(zhì)辦理
資質(zhì)辦理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投標(biāo)咨詢
投標(biāo)咨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證書查詢
證書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綠色報(bào)告查詢
綠色報(bào)告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