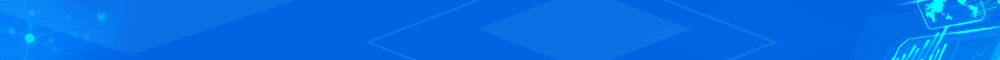【黔靈探理】從《古謝經(jīng)》看布依族死亡觀念及形成原因
所屬地區(qū):貴州 - 貴陽 發(fā)布日期:2025-05-06發(fā)布地址: 云南
【作者簡介】何嵩昱,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民族文學;鄧婷婷,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學關系、民族文化。
【基金項目】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重點項目“貴州布依族傳統(tǒng)生態(tài)文化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1GZZD62)的階段性成果。
【摘要】《古謝經(jīng)》是布依族文化經(jīng)典——“摩經(jīng)”中用于喪葬超度儀式的經(jīng)書,蘊含了布依族人對死亡的預設和遐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布依族的死亡觀念。《古謝經(jīng)》認為人的死亡只存在于肉體,而靈魂會永生。經(jīng)詞多次提及“靈魂”以及靈魂所歸之處,無論是天堂還是仙界,祖地還是陰間,皆是人世間的延續(xù),體現(xiàn)出布依族人“靈魂續(xù)世”的死亡觀念。這與最普遍最常見的“靈魂轉世”的死亡觀有所不同,是布依族人在獨特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制度以及民族信仰下形成的較為獨特的死亡觀。
【關鍵詞】古謝經(jīng);布依族;死亡觀念;靈魂續(xù)世
摩經(jīng)是布依族摩師用漢字和布依族古文字記錄下來并在布依族祭祀、喪葬、驅(qū)邪、祈福、禳災等場合中使用的成套經(jīng)書。一直以來,蘊含著布依族獨特的文化精神內(nèi)涵。摩經(jīng)分為用于喪葬超度儀式和用于祈福、禳災、驅(qū)邪等日常儀式兩類。摩經(jīng)中的《古謝經(jīng)》(也稱《殯亡經(jīng)》)是布依族用于喪葬儀式的經(jīng)典,其內(nèi)容宏大、想象奇特,既有先祖創(chuàng)世、靈魂跨界等奇幻描繪,也有釀酒擊鼓、染布織衣等族史回溯,體現(xiàn)出布依族人思維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此外,《古謝經(jīng)》有著包羅萬象的文化意象,指涉出布依族民眾關于死亡的集體想象。本文立足靈魂歸屬之地這一意象,探究布依族人如何想象死亡歸屬,如何描繪死后生活,以及這一想象和描繪體現(xiàn)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一、《古謝經(jīng)》中的靈魂歸屬之地
死亡是靈肉的分離。這是布依族民眾關于死亡最為基礎的想象,也是他們死亡觀念的一種體現(xiàn)。《古謝經(jīng)》關于死亡的描述并未停滯于此,而是在此基礎上更為細致地將人死后肉體和靈魂的發(fā)展路徑安排妥當。根據(jù)經(jīng)書的描述,亡者的肉體被置于棺木內(nèi),經(jīng)過多重吟誦、懷念儀式后轉而安置在摩師認可的墳地中。相比之下,靈魂的歸屬地則更為繁多,諸如仙界、天堂、新世間、祖地、陰間、地府等。靈魂歸屬地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仙界、天堂、新世間為主的富有美好色彩的地方;二是祖地、故土等具有家園情懷的地方;三是陰間、地府這類陰郁消極的地方。這三類歸屬地僅是表述不同,但它們最終指涉同一地方。
(一)仙界說
中國遠古神話、古籍中有“仙界”“仙境”等類似表達。《列子·黃帝篇》中將黃帝夢中的華胥氏國描繪為“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云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的奇幻之地,與仙界一樣混沌縹緲、寧靜美好。《莊子·逍遙游》將姑射山看作神人的棲息之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這增添了姑射山的神秘色彩。姑射山最初見于《山海經(jīng)》中,書中描述了姑射山三面環(huán)海,“無草木,多水”的地貌特點,使其從出現(xiàn)伊始便具有神秘朦朧之感。另外,《淮南子》中的“太帝之居”也是對“仙界”的想象與描繪:“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綜上所述,仙界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根源,它是生產(chǎn)力不發(fā)達時期人們對未知事物的描繪和想象,傾注了一定的情感色彩。
布依族在悠久的歷史發(fā)展中難免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因此出現(xiàn)仙界、仙家等道教概念也不例外。根據(jù)《漢語大詞典》:仙界是“仙人生活的地方”;仙家指“仙人所住之處。”《古謝經(jīng)》中將仙界表述為靈魂的歸屬地,實際上是將“靈魂”看作了仙。布依族人認為經(jīng)過摩師超度后的靈魂會進入仙界為仙。不同于上述古籍中“不食五谷,吸風飲露”,還擁有“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能力的神人,《古謝經(jīng)》中的仙有著如常人一般的生活方式及需求。書中在描述“仙”的生活時多次提到與食物相應的生產(chǎn)、生活資料,諸如“見拿桃花煮稀飯”中的“稀飯”,“天上有十塊九塊地,一塊栽苡仁米是老的”中的“苡仁米”,“用錢買上面那田壩……用錢買秧田”中的“田壩”和“秧田”等。可見,《古謝經(jīng)》中的仙也食五谷,他們與常人一樣需要食物以及田壩、田莊等。
《古謝經(jīng)》對仙家亦有詳盡描述:“仙家寬又寬,掃得很干凈等你,仙家闊又闊,留大屋等你,仙家有十寨九田莊,一田莊給你管,仙家管十街九街,一街給你逛,仙家管十城九城,一城給你管,仙栽竹建房,你栽竹建房,仙栽香樟造屋,你栽樟造屋,仙打擺酒桌,你打擺酒桌,仙討媳嫁女,你討媳嫁女。”從“寬又寬”“闊又闊”“大屋”“一田莊”“一街”“一城”可以看出,與人間相比,仙界的居住條件更好,物質(zhì)資料也更為豐富,但仙界的基礎構成與人間別無二致,即房屋、街道、田地等。此外,仙界的環(huán)境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通過“仙”從事諸如栽樹、建房等人類生產(chǎn)活動才得以建造。再者,“擺酒桌”“討媳嫁女”體現(xiàn)仙界延續(xù)了布依族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關系紐帶和風俗人情。
統(tǒng)而言之,在布依族的死亡觀念中,仙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神仙、神人,而是與常人生活方式幾近一致的人,略有不同的是,它們所處的仙界物質(zhì)資料更為豐富。《古謝經(jīng)》中靈魂歸屬到仙界,無論從靈魂的生活方式,還是仙界的整體樣貌,其敘述的是常人歷經(jīng)死亡、超度后靈魂在仙界的延續(xù)。
(二)祖地說
講述一段文明或一個民族常常會探尋其起源,其發(fā)端的地域常常成為尋根的關鍵,布依族也不例外。布依族多由遠地遷徙而來,因此祖地、故地、故土等類似語詞在他們的文學典籍、日常生活中時常被提及。對布依族族源的研究在改革開放初期蔚然成風,大致存在越族說、越濮說、濮萊說、羌越說等幾種說法。朱俊明在《牂柯越與東南越》中論證牂柯越人多“由嶺南溯右江或其它水道進入貴州”。“周氏在《駱越史初探》一文中,又論證駱越人是由‘柳江人’發(fā)展而來”。何光岳在《干越的來源和遷徙》中認為百越有不同的族源,“在古代各氏族部落的長期遷徙和來往交流中,他們之間,吸收了不少外族的成員”。由此可見,組成布依族的主要部落由外地遷徙而來這一觀點得到學界廣泛認可。這論證了《古謝經(jīng)》中的祖地并非子虛烏有的幻界,而是意指孕育民族的故土。因此,在想象死亡時,將祖地作為靈魂歸屬之地恰恰契合了布依族人尋根的原始愿景。
《古謝經(jīng)》敘述的祖地究竟為何物,又如何才能順利抵達呢?從指引亡者靈魂回歸故地的經(jīng)詞可以看到祖地的基本面貌:“矩州,讓寨主今天往哪里去呀?從普里到壩播、花約、年結……順著上去……那就是你要去自由住的地方,那州城就是你要去管理的州城,那地方就是你所尋覓的地方,那田莊就是你去管理的田莊。”去祖地要路過普里、壩播、花約、年結等地,向上走,那是一個有州城、田莊的自由地。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招魂并非亡者靈魂,而是摩師通過吟誦招魂經(jīng)、供奉活豬召回祖魂,期望先祖帶領亡靈走向祖地。
在布依族人看來,“送老去成仙,成仙靠祖父”。可見先祖的指引是靈魂成仙的重要途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祖父就是(先亡的)仙,祖地就是仙界。布依族世代的靈魂隨先祖走向祖地,“去歸同女始祖,去歸同老祖宗,去歸同老祖婆,去歸同人多在一起住”。“祖地”上已然形成了新的布依族族群。喪葬儀式宛如一道橋梁,為祖地的族群源源不斷地輸入新的力量。
“魂歸故地”是本民族對故土難離情懷的直接展現(xiàn),他們對祖地的想象并未添加太多的奇幻色彩,而是和仙界一樣,按照人世間的房屋構造和親緣模式等建構。其實,祖地宛如人間社會,親人朋友終將聚集于此,親緣關系從不間斷,這里是人世的延續(xù)。
(三)“陰間”說
《春秋左傳》有載:“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將黃泉看作人死后抵達之地,可見春秋時期便有了與陰間類似的黃泉概念。《禮記》“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提出安置魂魄于地。《史記》:“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提到陰間一詞。《后漢書》記載烏桓部落的喪葬時提到魂歸赤山之說:“俗貴兵死,斂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yǎng)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shù)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貸山也。”此處的赤山作為烏桓族人的靈魂歸屬之地,與泰山有著類似的作用。在這段時期,黃泉、陰間僅被看作人死后的歸屬地,沒有被賦予消極隱喻。爾后,佛教在中國的興盛以及道教文化傳統(tǒng)讓地獄、冥界、陰間衍生出許多民間故事,也將陰間加諸了磨難、陰郁、刑罰等消極意蘊。
布依族的陰間說類似于漢族經(jīng)典中的黃泉、陰間等概念,僅僅作為死后靈魂的歸屬之地,沒有優(yōu)劣善惡之分。《古謝經(jīng)》中有:“祖母成人去(去世),孝敬給祖母爭光,老人死到陰間去,挽塊孝帕敬祖母,孝心歸在孝詞中。”根據(jù)此經(jīng)詞所言,祖母去世后到了陰間,子孫在靈前表達孝心和敬意,并未有錯愕、恐懼之情,似乎一切皆在情理之中。“讓魂清白歸神簍,讓魂清白到陰府,讓親友高興”。從這句經(jīng)詞也可以看出,靈魂到了地府是令親友開心的事情,地府是靈魂樂于歸屬的地方。因此,《古謝經(jīng)》中的陰間、地府不僅不具有貶義,相反,它們是靈魂的好歸屬,像前面提及的仙界、祖地一樣。其實,布依族的死亡觀念里也具有貶義的游魂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有非正常死亡的人和其他未知來路的游魂,不同的死亡方式有不同的經(jīng)詞和祭品。譬如對非正常死亡的人要念誦一段《解難歌》才能召回墜入游魂世界的靈魂,使其回歸正軌。
總的來說,《古謝經(jīng)》中靈魂歸屬之地大致分為仙界說、祖地說和陰間說三類,它們在文本表述上較為含混,但其構建樣態(tài)幾近一致,即類似“人世間”。靈魂經(jīng)超度后,在旁仙(靈魂歸屬地)如生前一樣地生活,勞作生產(chǎn)方式、地緣血緣關系等無不體現(xiàn)出現(xiàn)世生活的延續(xù)性,故布依族的這一死亡觀念可稱為“靈魂續(xù)世”觀。
二、布依族“靈魂續(xù)世”觀的內(nèi)涵及特征
“靈魂續(xù)世”觀并非布依族所獨有,它產(chǎn)生于人類共通的情感中,即本能的求生欲望和對親緣關系的眷念之情,因此普遍存在于許多民族中,譬如陪葬、殉葬現(xiàn)象便是一種續(xù)世想象,這是廣義的“靈魂續(xù)世”觀。狹義的“靈魂續(xù)世”觀形成于不同的地域和文化中,表現(xiàn)出獨特的民族性,例如與帝王豐厚的陪葬品所折射出的個體性行為相比,布依族喪葬儀式中焚燒的農(nóng)具等物品是受族群團結共事的影響,體現(xiàn)出更多的群體特征,這就是狹義的“靈魂續(xù)世”觀所體現(xiàn)的差異性。
布依族的“靈魂續(xù)世”觀是群體性意識構筑的,族群的生生不息是其建構重點。它還有一個較為重要的特點是將祖先崇拜發(fā)揮到極致,使祖先具備了崇高的地位。此外,布依族的“靈魂續(xù)世”觀立足本民族特色,有著更為細致的建構方式,囊括了歸屬路徑的多個節(jié)點,其幾近一個完整的死亡體系。在“靈魂續(xù)世”視閾下,布依族人將喪葬儀式看作“靈魂”的新生,又將靈魂看作生命的續(xù)啟,于是歷時地構筑了永生的族人,也建構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總的來說,“靈魂續(xù)世”相對于“靈魂轉世”而提出,祖先是其續(xù)世的核心驅(qū)動力,它促使靈魂代替肉身在旁仙生活以延續(xù)個體生命體驗,這一死亡觀念具有延續(xù)性、教化性、神秘性和象征性四個特征。
(一)延續(xù)性
“靈魂續(xù)世”觀的一大特征是其具有延續(xù)性,這并非延續(xù)物質(zhì)上的肉身從而使人永生,而是在形而上層面以構思、體驗等方式使個體的兩段生命在不同維度上一以貫之,從而形成線性的生命長河。當然,無數(shù)的個體會聚成集體,其延續(xù)的對象也從個人上升至族群。
從個體角度來看,“靈魂續(xù)世”觀的連續(xù)性體現(xiàn)在個體生命體驗上,它歷時性地勾勒出以喪葬儀式為續(xù)接點的生命長河。首先在于個體記憶得以延續(xù)。《古謝經(jīng)》中:“吃著看兒媳婦,兒媳婦在舂碓,吃著看姑爺,姑爺在劈柴禾……吃著看女兒,女兒在舂碓,吃著看男兒,男兒在劈柴禾”。這段經(jīng)詞講述了摩師眼中的亡者靈魂一邊吃著亡靈飯,一邊不舍地環(huán)視眾親友的場面。從“看兒媳婦”“看姑爺”“看女兒”“看男兒”幾個動作描寫可以發(fā)現(xiàn),布依族人認為人死后記憶不會消逝,即便成為靈魂也依舊存有生前的血緣、地緣人際關系的記憶。這一記憶的延續(xù)使得布依族人并不畏懼死亡,相反,死亡后可以與已逝的親友相聚,終有一天也會與生前的親友相逢,旁仙與其說是死亡所歸之地,不如說是一個永恒的人世間。
其次是個體生活方式的延續(xù)。在布依族人的意識中,“靈魂”在另一個世界的經(jīng)濟行為、生產(chǎn)行為如人世間一樣。其實喪葬過程的許多內(nèi)容是為了讓死者在另一個世界很好地生活而進行鋪墊,例如所燒紙錢是給亡者在另一個世界使用,這就體現(xiàn)出貨幣商品經(jīng)濟和流通方式的延續(xù)。此外,喪葬儀式中靈桌旁有竹制的犁耙和豎鐵三角、鐵鍋、簸箕、甑子、壇子、鏵口等生產(chǎn)、生活用具,布依族認為,死者到陰間也同樣要這些工具來從事勞動和生活。從犁耙、豎鐵三角、鏵口等農(nóng)具可見,亡者在“旁仙”依舊以農(nóng)耕生產(chǎn)為主;從鐵鍋、簸箕、甑子等廚具得知,旁仙的主要物質(zhì)資源依舊是稻米等糧食作物。綜上所述,不論是經(jīng)濟行為還是生產(chǎn)行為,皆體現(xiàn)出個體生活方式的延續(xù)。
個體記憶和生活方式的延續(xù)指向了布依族群體樣態(tài)的延續(xù),表征出整個民族的生存動向。除了生存層面,“靈魂續(xù)世”觀還延續(xù)了布依族的精神旨歸,將布依族的民間信仰延續(xù)至旁仙。從《古謝經(jīng)》中祖先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見出旁仙中的敬祖:“送老去成仙,成仙靠祖父。”這體現(xiàn)了祖先對亡者靈魂成仙具有的引領作用,彰顯了祖先在靈魂歸仙之路中的崇高地位。尊師亦延續(xù)至旁仙,經(jīng)師能夠溝通現(xiàn)世與來世兩界,超度“靈魂”使其順利歸屬至旁仙。另外,相傳報勒陀(傳說是摩教的創(chuàng)立者,布依族尊奉其為經(jīng)師祖)創(chuàng)造了田和梯坎,這對布依族來說無異于是創(chuàng)世之舉,因為布依族是水稻民族,田和梯坎是其民族生存之本,對延續(xù)農(nóng)耕生活的旁仙來說也是如此。
由上可見,無論是生存層面的生命記憶還是生存方式,抑或精神層面的“尊師敬祖”,皆從生前延續(xù)至死后,體現(xiàn)出跨越生死的延續(xù)性特征。
(二)教化性
構設未知的靈魂和死后的生活往往可以規(guī)范現(xiàn)世行為,《圣經(jīng)》如此,《古謝經(jīng)》亦是如此,這便賦予“靈魂續(xù)世”以教化色彩。它通過傳遞神秘、恐懼、憧憬等情感,將個體生命的路徑展現(xiàn)于世人眼前,尤其是旁仙的生活以及潛藏于其間的道德倫理,一定程度上可以約束和規(guī)范布依族人的行為。
“靈魂續(xù)世”不僅體現(xiàn)了精神信仰的延續(xù),還不斷強化這一觀念。上文提到“尊師敬祖”是布依族族群跨越生死的精神旨歸,這不僅于延續(xù)中貫穿族群信仰,還在崇高、宏大的敘事中不斷強化這一精神觀念,潛移默化地教化世人遵循。《古謝經(jīng)》多次將祖先置于宏大的敘事中:“布靈最勤快。布靈最聰明,他來造成天,他來造成地。”布靈和勒靈創(chuàng)造了自然萬物,勾勒出宏偉的宇宙圖譜。經(jīng)詞所描繪的先祖幾近于創(chuàng)世者,是萬物之始,“靈魂續(xù)世”的“世”便是先祖所創(chuàng)之世的延續(xù)。從這個角度來說,“靈魂續(xù)世”以死的生活反哺生的生活,強化了尊師敬祖的倫理觀念。
將仙賦予勤勞美好的品質(zhì),以教化世人勤勤懇懇地生活。仙在前面有所提及,是經(jīng)摩師超度后進入旁仙的靈魂,這是布依族人認為的死后應有的歸宿,因而仙具有了一定的價值導向作用。仙(與祖先同)不僅承擔著引領靈魂歸于旁仙的重要職責,還具有栽樹造房、打桌擺酒、栽秧請客等勤勞質(zhì)樸的美好品質(zhì)。“靈魂續(xù)世”觀從側面告知世人,縱向上勤勞生活貫穿人之一生,橫向上仙、人平等地要通過勞作換取生活資料。總的來說,“靈魂續(xù)世”觀不斷地強調(diào)勤勞善良等美好品質(zhì),并以此規(guī)范、教化世人行為。
將自然萬物注入靈性色彩,讓尊重、愛護自然的意識深入人心。靈魂能夠續(xù)世并非沒有條件,上文提及的超度儀式是必經(jīng)之路。這一儀式中有一環(huán)節(jié)是立龍戈,即選擇一根合適的竹子作為靈魂去往旁仙的橋梁,《祭靈經(jīng)》中也提道:“金竹生野外,好拿做魂竿,斑竹生野外,好拿立魂竿。”在布依族觀念中,竹是有神性的,人的靈魂由竹而生,年老逝世隨竹升天,人的生存也要由竹保佑。在這一觀念籠罩下,布依族民眾對竹木的砍伐十分謹慎,因為他們害怕侵擾到竹魂以損傷自我。在萬物有靈的沁潤下,畏懼成為情感召喚的基礎,尊重、愛護自然的意識潛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三)神秘性
死亡是人類未知的領域,因而關于死亡的論述富有較強的想象性和主觀性。布依族的“靈魂續(xù)世”觀也不例外,它在人世間的基礎上加以幻想,以此建構了旁仙。無論是旁仙之地還是歸屬過程,皆充滿神秘色彩。
在布依族的死亡觀念中,靈魂歸屬旁仙需要特定的超度儀式,這種儀式稱為古謝,整個古謝儀式充滿了神秘性。例如摩師能夠看到世人看不到的靈魂:“無誰從黑處來吃,只有你從黑處來吃,無誰來吃亡靈飯,只有你跨過來吃亡靈飯,無誰從壁笆來吃,只你從壁笆上來吃,無誰從房屋的半空中來吃,只有你從房屋的半空中來吃,無誰跑從荒壩上來吃,只有你跑從荒壩中來吃,無誰躲著眾人來吃,只有你躲著眾人來吃。”這段經(jīng)詞講述的是亡者靈魂在古謝儀式上吃亡飯的場景,亡者靈魂“從黑處來”“跨過來”“從壁笆來”“從房屋的半空中來”“從荒壩上來”“躲著眾人來”等行為是無規(guī)律的、不可見的,而且在敘述上是重合、矛盾的,也是異于常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超度儀式具有神秘色彩。
靈魂經(jīng)由超度便開啟了去往旁仙的旅途。“那里你未知,你盡管走去,越走下越遠,越走上越寬,腳越向前走,走到第一路,此路走你的地,走到第二路,此路走你田,走到第三路,此路見魚肉,走到第四第五路,此路見朋友”。去往旁仙的路程神秘且曲折,分別有五條路,越走越寬、越走越遠,沿途的風景也混亂無序,諸如田、魚肉、朋友之間沒有邏輯聯(lián)系。亡者靈魂繼續(xù)走,所看到的物象越加奇特,尤其是“臉嘴花又花,花稍嘴吃人,臉像蘭靛花,花嘴會吃人,面孔像鴨肉白,面孔象雞肉白”的巫婆,難免給人神秘之感。
而后,靈魂到了旁仙,它是一個類似人世間的地方,但與人世間不盡相同,旁仙更具神秘氣息。一是體現(xiàn)為旁仙的州、城、寨、河等基礎建設較之人世間更為恢宏,個人所得的物質(zhì)資料也更加豐富:“天上有十寨九河,青魚花魚河是我老的,天上有十園九園,一園晾衣晾麻是老的,天上有三百匹壯馬,一馬歸老騎……天上有一百五十個州城,一城歸老管。”二是體現(xiàn)在旁仙異于人世間獨特的風景,不再是州城建設,而多了主觀構建的層級,以及每一層相對應的自然風光:“走到三百塊田壩,一田三個井,水落田不現(xiàn)……上走三層見太陽,上走七層見雪花”。三層、七層等關于旁仙的構想使其增添了神秘色彩。此外,從經(jīng)詞中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難以解釋的現(xiàn)象,譬如“水落田不現(xiàn)”這一景觀難以用常理解釋,水如何落下,田又如何隱蔽給予了人們想象空間,體現(xiàn)出濃郁的神秘色彩。
從超度儀式,到歸祖之路,再到旁仙環(huán)境,其作為“靈魂續(xù)世”的起點、過程和終點,勾勒了續(xù)世后完整的生命路徑,其敘述過程中加入了想象性建構,顯露出了神秘的氣息。
(四)象征性
“靈魂續(xù)世”是布依族民眾面對死亡這一未知領域體現(xiàn)出的樸素的唯心主義觀點,是立足個體生存境況和民族發(fā)展趨勢而闡發(fā)的,因而對個體和民族具有雙重的象征意義。
一方面,“靈魂續(xù)世”通過將個體生命無限延長來表現(xiàn)其生命的永生。“靈魂續(xù)世”不同于“靈魂轉世”所述之墜入六道輪回后重新開啟新的一世,它強調(diào)的是個體生命的唯一性和永恒性。“靈魂續(xù)世”將生命劃分為首尾相接的兩段,第一段是個體在人世間的生活,它的終點是死亡;第二段是繼死亡、超度后的靈魂,它生活于旁仙,沒有終點。就像《古謝經(jīng)》中所述:“萬代居那里,萬年住那里。”這是對永生的最好注釋,是“靈魂續(xù)世”觀于個體層面的象征。
另一方面,“靈魂續(xù)世”通過對個體生命永生的描述,以及靈魂歸屬旁仙的程式,構筑出生生不息的族群。靈魂聚集于旁仙,逝去的族人皆在此相聚,且隨著時間的流逝,靈魂的數(shù)量越來越多。由于記憶的延續(xù),血緣、地緣關系也延續(xù)至旁仙,旁仙中族人靈魂的數(shù)量以及它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已然能夠稱之為布依族族群網(wǎng)絡的延續(xù),在靈魂永生的基礎上,族群也不會消逝。另外,前文提及在旁仙中“栽樹造房“釀酒擊鼓”“擺酒吃飯”“接媳嫁女”等皆延續(xù)了布依族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因而可以說,個體生命永生也將具有布依族特色的生活方式永遠地存續(xù)下來。
“靈魂續(xù)世”下的古謝儀式宛如一道橋梁,為旁仙的族群源源不斷地輸入新的個體力量,并隨時間發(fā)展愈加壯大。因此,人不會消亡,靈魂會在旁仙繼續(xù)生活;家庭不會消散,父母孩子終將在旁仙團聚;族群不會滅亡,他們會在旁仙日益壯大。
三、布依族的“靈魂續(xù)世”觀念的形成原因
“靈魂續(xù)世”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靈魂續(xù)世”觀產(chǎn)生于人類共通的情感中,于許多民族所共有,是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體現(xiàn);狹義的“靈魂續(xù)世”觀具有差異性,形成于各民族獨特的環(huán)境中,這既包括自然環(huán)境,又包括人文環(huán)境。
(一)地理環(huán)境:偏遠封閉與依山傍水
貴州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的省份,由于地理環(huán)境封閉、偏遠、險峻,使得聚居于此的布依族形成了較為穩(wěn)定的生產(chǎn)方式、社群關系以及思維結構。他們恪守祖宗遺訓,堅守土地和家園,對自身文化的建構和表達也是基于本民族的習俗及信仰,因而他們以本民族為主要參照物架設旁仙生活。例如用竹子和香樟建造房屋的場景:“仙栽竹建房,你栽竹建房,仙栽香樟造屋,你栽樟造屋”;造酒的場景:“拿酒飯在缸里發(fā)酵,拿酒飯放在有蓋的缸里蓋好,要用三場多時間,要用五場多時間,成酒釀滴落下來,成輕飄的酒飯浮上來”等,再現(xiàn)了布依族的現(xiàn)實生活。甚至在《古謝經(jīng)》中出現(xiàn)以本族生存方式想象其他民族的經(jīng)詞,例如“經(jīng)師會看地,八卦師會看地,儂寨師會看地,漢寨師會看地,苗寨師會看地”。
此外,靈魂歸于旁仙的路程遙遠且神秘,但其提及的地名多數(shù)可考,“讓寨主今日往哪方去?矩州,普里,井口、花作、戛所、坉上”。這句經(jīng)詞的注釋說到上述地名是扁擔山區(qū)內(nèi)的地名,這論證了布依族是參照本族所處地理位置來構建歸仙之路的觀點。最后,較為封閉的生活環(huán)境促使他們以自發(fā)性、主觀性、復魅化的方式去闡釋未知領域,將精神寄托于已逝祖先和通靈摩師之上,用儀式、想象等方式實現(xiàn)對永生的向往,這逐漸形成了“靈魂續(xù)世”的死亡觀念。
布依族村落的選址通常位于峰叢低谷中,地勢較為平整,且旁邊有河流流經(jīng),水源充足。除此之外,布依族生活的地區(qū)多屬中、北亞熱帶濕潤氣候區(qū),熱量充足,雨量充沛,雨熱同季,終年溫暖濕潤,年平均溫度為16℃左右,年降雨量在1000~1400毫米之間。多雨濕潤、溫度適宜的地理環(huán)境有利于水稻生長,《黔南識略》載“貴陽則青仲也,善治田”。因此布依族又被稱為“水稻民族”。在以農(nóng)耕為主的環(huán)境下逐漸形成了布依族人濃厚的土地意識,他們將耕作看作生存的基礎,也十分珍惜自然賦予的物質(zhì)資料,這就不難理解為何靈魂到了旁仙也需要農(nóng)具進行勞作生產(chǎn)。
總的來說,布依族長期生活的地理環(huán)境呈現(xiàn)兩大特點:一是偏遠封閉,這使得布依族先民在信息閉塞的環(huán)境中形成以自我觀照未知領域的思維方式,因此構筑出以本民族為基礎的旁仙;二是依山傍水,這為種植水稻等農(nóng)作物提供了條件,也滿足了他們對現(xiàn)世物質(zhì)資料的需求,因此,將這一生產(chǎn)方式延續(xù)至旁仙也符合布依族民眾的原始愿景。
(二)社會制度:宗族制和議榔制
布依族歷來有著十分森嚴的氏族管理制度,并形成了以宗族制為核心的家族管理模式。宗族通常“由同宗同姓的一個或數(shù)個村寨組成,各地皆然。其血緣聯(lián)系緊密,內(nèi)部禁止通婚,每個宗族都有族長(自然領袖)”。這促使他們堅守不可逾越的祖先后輩關系,為“靈魂續(xù)世”觀中生命的唯一性提供了思想來源。此外,宗族的族長通常由輩分較高并有威望的人擔任,他們對內(nèi)教化、規(guī)約族人,對外代表本宗族的利益談議大事,這實則是祖先崇拜的多維體現(xiàn)路徑之一。《古謝經(jīng)》中提到“那就有管事的祖下凡”中管事的祖,一定意義可以看作族長的延續(xù),因此,“靈魂續(xù)世”觀中隨祖先升天的行動軌跡便可以看作是在族長的帶領下發(fā)生的,“靈魂續(xù)世”觀也在宗族制的灌溉下形成。
布依族先民輾轉多地才找尋到貴州山區(qū)定居,并在此繁衍生息。隨著時間的發(fā)展,險峻封閉的地域環(huán)境促使布依族實行自給自足、自我管理的社會組織形式,并由此形成了議榔制。“‘榔’源于布依族早期社會的血緣組織,又是本族群眾對部落酋長的稱謂。隨著社會發(fā)展,逐步變?yōu)橐缘鼐夑P系為聯(lián)系的農(nóng)村公社組織”。承擔起制定村規(guī)民約,約束、管理村民的重任。從某種意義上說,榔是超越血緣關系的、管轄范圍更大的族長,這再次強調(diào)了祖先在布依族中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議榔制為布依族人營造了和諧安穩(wěn)的族內(nèi)環(huán)境,滿足了布依族安居樂業(yè)的原始愿望。議榔制立足血緣地緣的人際關系,從自我管理的角度出發(fā),因其更貼近本族人,也更為了解他們需求,得到了族人的擁護,最終更為民主、有效地實行了日常管理。冊亨布依族石碑刻文:“人家有規(guī),敬老慈幼,勿忘賓禮。”“處鄰里而和鄉(xiāng)黨,莫使愧心而昧騙”“富貴貧賤、紅白會期,□□(扶幼)助老,鄰里相幫,一境和悅。”由此可見,在議榔制下,布依族社會環(huán)境安寧、穩(wěn)定,人際關系和諧,大家互幫互助、團結友愛。安定和諧的生活氛圍讓布依族人希冀死后依然能如此,因此他們在建構旁仙生活時便延續(xù)了現(xiàn)世生活的血緣、地緣人際關系,以及管事祖先對眾“靈魂”的管理。
宗族制和議榔制為布依族創(chuàng)造了安居樂業(yè)、民主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這也成為了布依族先民想要延續(xù)現(xiàn)世的契機。此外,這兩種民主自治制度形成了以宗族制為核心的家族自我管理和以議榔制為核心的村寨自我管理模式。它們有一個共通點,即推選有威望的長者擔任管理者,這體現(xiàn)出布依族人在血緣、地緣關系下對祖的尊敬,一定程度上促使族人在“靈魂續(xù)世”中將祖先作為“靈魂”的引領者。
(三)精神信仰:“尊師”與“敬祖”
師和祖是布依族的精神信仰,也是“靈魂續(xù)世”觀中的驅(qū)動性力量。師即摩師,祖即祖先,他們不僅是一種稱謂,更是族群精神力量的化身,寄托了布依族的崇敬和信仰。
布依族十分尊崇摩師。摩師是布依族中摩教的職業(yè)者與傳承者,多為自然領袖,主要為村寨、宗族群體或家庭主持喪葬儀式或為人們祈福禳災等。相傳摩教的開山祖師是報勒陀,他充滿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能洞察周遭一切事物,保護布依族子民不受邪氣侵擾。時至今日,布依族在三月三、六月六等祭祀中都會敬拜這位創(chuàng)世祖。布依族先民將族群中出現(xiàn)的災難歸因于超自然力量,并認為只有摩師舉行儀式才能驅(qū)除邪氣,恢復生活的和諧安寧。由此可見,布依族民眾對摩師的崇敬在日常生活中常有體現(xiàn),并將這一崇敬延續(xù)至旁仙。此外,《古謝經(jīng)》是布依族進行超度儀式不可或缺的經(jīng)書,經(jīng)書文字是布依族先民借漢字語音和偏旁組成的,由于這些文字符號并非官方的、統(tǒng)一的,加之在傳承、抄錄的過程中難免有所失落,故而導致了文本的斷續(xù)和模糊。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那些經(jīng)驗老到的摩師才能憑借自身的理解補充文本的空白部分,故摩師占據(jù)著喪葬儀式的重要位置,這對開啟“續(xù)世”階段至關重要。
在布依族的精神信仰中,“摩師”還能夠“通靈”。譬如《古謝經(jīng)》中摩師會算命、喊魂:“我本會算命,我本會喊魂。”會看見“靈魂”:“神走巫到門口,你就到窗口,神巫就到窗口,你轉到門坎。”會與“靈魂”溝通:“要你來這里聽我講幾句,你大膽點過來貼近胸口來聽,豎起耳朵來聽。”可見,布依族人信仰摩師也就等于間接認同了靈魂之說。在生產(chǎn)能力、認知能力較為低下的遠古時期,布依族先民對自然的認識尚且不足,于是他們以主觀意識為闡發(fā)基礎,構想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一定程度上實現(xiàn)了“靈魂續(xù)世”觀的合理性。
祖先在“靈魂續(xù)世”觀中無處不在,如果說摩師是開啟靈魂續(xù)世的執(zhí)行者,祖先便是這一動態(tài)行為中的先行者和引領者,它直接促使了靈魂的延續(xù),跨越了生死之限。例如人死后“去歸同女始祖,去歸同老祖宗,去歸同老祖婆,去歸同人多在一起住。”論證了“靈魂續(xù)世”觀中亡者靈魂隨祖先們永生地生活在旁仙;再例如“祖宗和祖宗,祖位在黑殿,捧鮮花來接,祖宗和祖宗,祖位在明宮,吹嗩吶來接”。可見靈魂想要升仙離不開祖宗的指引。其實在許多布依族的節(jié)日、祭祀中都體現(xiàn)出族人對先祖的敬重,譬如“二月二”有著殺雞敬祖的傳統(tǒng),如此的祖先信仰、崇拜形成了“靈魂續(xù)世”觀中各異的旁仙別稱——祖地、祖墳、祖位、祖根。
布依族“尊師敬祖”的精神信仰從兩方面塑造了“靈魂續(xù)世”觀,一方面是將摩師所具有的通靈、奇幻等超現(xiàn)實現(xiàn)象投射于人的意識中,以此建構靈魂、旁仙等具有想象性的概念,并以個體的生命將其貫穿為一個完整的體系;另一方面是把祖先放置于關鍵位置,以此生發(fā)出以祖先為驅(qū)動力的“靈魂續(xù)世”觀。
四、結語
布依族的“靈魂續(xù)世”觀否定享樂式成仙,也排斥通過苦難磨練心智,傳達出對現(xiàn)世的不舍,也表達了對死亡的接受。這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儒家“生死可續(xù),仁愛蒼生”的死亡觀念。另外,“靈魂續(xù)世”觀中對祖先、宗族的尊敬,以及對品德的要求與儒家的忠孝觀、仁義觀幾近一致。儒學作為漢族文化的代表,自漢代開始傳播至貴州境內(nèi),明初時期封建王朝加強了對民族地區(qū)的儒學教化。由此可見,布依族“靈魂續(xù)世”觀的形成極有可能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其實各個民族、各個時代皆有關于死亡的想象,布依族的死亡觀念將靈魂歸屬至旁仙,個體上升至群體,構筑永生個體的同時還建構出生生不息的民族。究其原因,以水稻種植為生的布依族在共事勞作的生產(chǎn)方式,共建房屋、共御外敵的生存方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需要團體協(xié)作,于是乎形成了集體主義思想。這也是農(nóng)耕文明下的必然產(chǎn)物,一定意義上實現(xiàn)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大一統(tǒng)”觀念的地域性呼應。正如***總書記所言:“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
編輯說明:文章來源于《貴州民族研究》2024年第5期。原文和圖片版權歸作者和原單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釋從略。
主 ? ? ?編:劉 ? 榮 ? ??
副 ?主 編:高登榮 郭飛平 楊文順?
? ? ? ? ? ? ? ?黎貴優(yōu) 高 ? 朋
執(zhí)行編輯:吳 ? 鵬 賈淑鳳
編 ? ? ?輯:李全敏
編輯助理:羅春燕
您的稿件和服務意見請發(fā)往"民族學與人類學"微電子雜志服務郵箱: [email protected] ? ? ? ? ? ? ? ? ? ??
您的支持和鞭策將會是我們進步的源動力!
“民族學與人類學”
民族學與人類學
Minzuology&Anthropology

![]() 關注微信公眾號
關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查看免費推送
- 貴陽招標網(wǎng)
- 遵義招標網(wǎng)
- 安順招標網(wǎng)
- 銅仁招標網(wǎng)
- 畢節(jié)招標網(wǎng)
- 六盤水招標網(wǎng)
- 黔西南招標網(wǎng)
- 黔東南招標網(wǎng)
- 黔南招標網(wǎng)
- 樅陽縣招投標中心
- 廣州奧天海鵬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 梅州梅縣華僑中學招標網(wǎng)
- 無錫工程造價信息網(wǎng)
- 呼倫貝爾市人民政府
- 河北應急廳
- 宿州公共資源交易網(wǎng)招標
- 來賓招標網(wǎng)
- 棚改招標
- 陪標出場費一般是多少
- 東光縣財政局
- 南京政治學院
- 西南|采購網(wǎng)招標公告
- 高陵區(qū)招標
- 明光市工程建設招標網(wǎng)
- 合川市信息網(wǎng)
- 撫順市建設工程招標網(wǎng)
- 攝像機招標
- 南皮縣教育局
- 臨汾招標信息網(wǎng)
- 廣東建設網(wǎng)
- 中國科學院中關村醫(yī)院
- 海安政府招標網(wǎng)
- 那曲招標投標公共服務平臺
- 永修縣招投標中心
- 陜西招標與采購網(wǎng)招標公告
- 三沙市招投標中心
- 招投標收費管理辦法
-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招標信息公示網(wǎng)
- 秦皇島財政招標
- 滎經(jīng)縣招投標中心
- 寧夏工程建設招標采購公共平臺
- 浙江省招投標信息網(wǎng)
- 江蘇思源赫茲互感器有限公司
- 灤州市招投標中心
- 保潔招標公告
- 南師附中宿遷分校
- 濟陽縣招標
- 北京市東城區(qū)花市小學
- 河南省政府采購網(wǎng)招標投標
- 鐵嶺市人民政府
- 陜西省招標信息公示網(wǎng)
- 孟津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招投標知識點和重點
- 云南機電職業(yè)技術學院
- 天津美術學院
- 任丘市政府網(wǎng)
- 第|十三飛行學院
- 澠池縣人民政府
- 岱山教育網(wǎng)
- 金鄉(xiāng)招標采購信息
- 營口招標公司
- 廣西科聯(lián)招標中心有限公司
- 揭陽招標網(wǎng)
- 遼寧政府|采購招標中心
- 招標采購公司有哪些
- 南陽市高新區(qū)
- 嵩明縣人民政府
-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
- 增城區(qū)財政局
- 電器采購招標文件
- 銀行培訓招標
- 句容市教育局
- 定海區(qū)教育局
- 土購網(wǎng)|信息
- 涼城縣應急管理局
- 徐州建筑招標
- 采購管理ERP
- 安徽采購與招標網(wǎng)
- 遼寧建設工程信息交易網(wǎng)
- 惠東縣惠東職業(yè)中學
- 陽谷縣教育局
- 四川政府采購網(wǎng)招標采購
- 學校招標文件
- 梅江區(qū)人民政府
- 遼陽招標采購網(wǎng)
- 中煤陜西公司招標網(wǎng)
- 單縣招標網(wǎng)
- 施工總承包招標文件
- 昆山招標信息
-
 聯(lián)系客服
聯(lián)系客服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信息發(fā)布
信息發(fā)布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招標訂閱
招標訂閱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商機挖掘
商機挖掘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數(shù)據(jù)定制
數(shù)據(jù)定制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標書代寫
標書代寫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資質(zhì)辦理
資質(zhì)辦理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投標咨詢
投標咨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證書查詢
證書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綠色報告查詢
綠色報告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