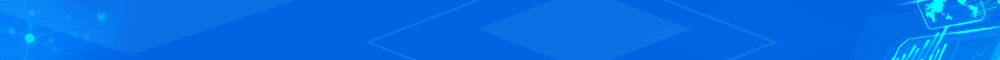《音樂文化研究》:楊民康 | 古代“南方-海上”絲路“神、佛、雅、俗、土”器樂分類的歷史發(fā)展與演變過程
所屬地區(qū):浙江 - 紹興 發(fā)布日期:2025-01-13音樂絲綢之路研究
本文刊載于:
2024年第4期,第7-17頁
古代“南方-海上”絲路“神、佛、雅、俗、土”器樂分類的歷史發(fā)展與演變過程*
楊民康
內(nèi)容提要:
古代“南方-海上”絲綢之路音樂文化中的傳統(tǒng)器樂,涉及一個包含“神、佛、雅、俗、土”五種分類的器樂文化系統(tǒng),其中的世俗性或藝術(shù)性部分如今更多演變并歸結(jié)至一個由雅(細(xì)樂)、俗(粗樂)兩個子系統(tǒng)構(gòu)成,并與戲劇、舞蹈、聲樂緊密結(jié)合的“‘歌、舞、樂’三位一體”的完整樂舞文化系統(tǒng)。傳統(tǒng)器樂的“雅、俗”分類,在古代較多涉及官方(或?qū)m廷)文化與民間文化的縱向階層關(guān)系,如今則更多指一種建立在縱橫相間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基礎(chǔ)上的較新的社會階層關(guān)系,在古代印度和中國的宮廷音樂中同樣存在較明顯的文化痕跡和發(fā)展、演變軌跡。
關(guān)鍵詞:
“南方-海上”絲路;“神、佛、雅、俗、土”器樂分類;神樂;俗樂;粗樂;細(xì)樂
作者簡介:
楊民康(1955—),男,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特聘教授,中國音樂學(xué)院特聘研究員,哈爾濱音樂學(xué)院特聘教授,中央音樂學(xué)院研究員、博士研究生導(dǎo)師(北京,100031)
項目基金:
本文系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藝術(shù)學(xué)項目“南方跨界族群音樂民族志的理論建設(shè)和選點(diǎn)、比較研究”(項目編號:20BD06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在古代“南方-海上”絲綢之路沿線,隨著南傳佛教和印度教的傳播,從南亞、東南亞到云南傣族地區(qū)分布著大量的傳統(tǒng)樂器和器樂表演形式,所形成的區(qū)域文化特征,可用帶有“印度化”色彩的“神、佛、雅、俗、土”分類予以概括。應(yīng)該說,這個分類體系并非是指某一個歷史發(fā)展時期或時間段特有的現(xiàn)象,而是對這一區(qū)域文化領(lǐng)域長期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曾經(jīng)發(fā)生和出現(xiàn)過的不同器樂因素的一個歷時性概括。本文將對上述狀況展開梳理和討論。
一、前現(xiàn)代時期以來 “南亞-東南亞”“神樂、俗樂”區(qū)域性特征的形成與發(fā)展
古代“南方-海上”絲綢之路音樂文化有著長期而錯綜復(fù)雜的歷史發(fā)展過程,若論其傳統(tǒng)器樂沿襲至今的較具有代表性的區(qū)域文化特點(diǎn),并非僅僅是指以某一兩件樂器或一兩個樂種為代表的純器樂表演類型,而是涉及了一個包含“神、佛、雅、俗、土”五種分類的器樂文化系統(tǒng)。在如今傳統(tǒng)文化中信仰與世俗或宗教與藝術(shù)等二元對立因素明顯分化、分離的情況下,其中的世俗性或藝術(shù)性部分,更多演變并歸結(jié)至一個由雅(細(xì)樂)、俗(粗樂)兩個子系統(tǒng)構(gòu)成,并與戲劇、舞蹈、聲樂緊密結(jié)合的“‘歌、舞、樂’三位一體”的完整樂舞文化系統(tǒng)。這里所指的雅、俗兩個子系統(tǒng),在古代較多涉及官方(或?qū)m廷)文化與民間文化的縱向階層關(guān)系,如今則更多指一種建立在縱橫相間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基礎(chǔ)上的較新的社會階層關(guān)系。由此看,“雅、俗”兩類器樂,在古代印度和中國的宮廷音樂中同樣存在較明顯的文化痕跡和發(fā)展、演變的軌跡。
在早期東南亞歷史上,伴隨著古代印度文明向東北方向的傳播,“南方-海上”絲綢之路曾經(jīng)經(jīng)歷了一個重要的“印度化”社會文化發(fā)展階段,其器樂文化的發(fā)展及雅(細(xì)樂)、俗(粗樂)分類的形成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度形成了一種神樂、佛樂、雅樂和俗樂并存與對立的藝術(shù)文化系統(tǒng)或社會制度。其中,神樂和俗樂是較早發(fā)生和存在的一對音樂(或器樂)關(guān)系類型。
(一)古代南亞地區(qū)的神樂與俗樂分類體系
在本文所謂的“神、佛、雅、俗、土”音樂(或器樂)分類中,又可以宗教音(器)樂和世俗音(器)樂再分為兩大類。其中,宗教音(器)樂包括神樂和佛樂,神樂以印度教儀式音樂為主。就此,有必要追溯一下“印度化”潮流的源頭——印度文化中的神樂與俗樂劃分觀念。
在南亞地區(qū),印度教產(chǎn)生的時間早于佛教,其儀式音樂的歷史也比佛教音樂更為悠久。在婆羅多《舞論》第五章“序幕規(guī)則”里提及,當(dāng)時為了贊頌天神,以那羅陀等樂師以變化式和靈活式風(fēng)格演奏七種傳統(tǒng)歌曲、前奏、戲外歌,這里涉及的應(yīng)該就是與聲樂表演相關(guān)的神樂(或雅樂)和俗樂。另外,根據(jù)《舞論》所載,古代印度音樂里,當(dāng)時所用的樂器和適用的表演場合也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宗教祭典和官方儀典中的用樂,“吹響螺號,敲響天鼓、穆丹迦鼓和腰鼓,舞臺上應(yīng)在所有樂器的伴奏中表演戰(zhàn)斗”[1]。另一類是宮廷內(nèi)部日常使用的宴享和官(皇)民共享的節(jié)慶禮儀用樂。筆者借用古代中國的分類思維,將之歸于神樂和俗樂,后者又可以根據(jù)審美性質(zhì)再分為雅樂和俗樂,或根據(jù)社會功能區(qū)分為宮廷器樂和民間器樂(含民間祭祀器樂)。其中由嗩吶和鼓組成的神樂樂隊的組成狀況和社會作用,除了在《舞論》古代石窟壁畫里已有記載和描繪外,還在今天南亞、東南亞的印度教和佛教寺院里繼承了下來。
關(guān)于神樂,可以發(fā)現(xiàn)在由古至今有關(guān)印度教的各種資料里,像上述《舞論》所描述的,在相關(guān)祭祀活動中采用由嗩吶和鼓、鈸等打擊樂組成的吹打樂幾乎是很少例外的標(biāo)配。而如今在東南亞和云南地區(qū)普遍存在的鑼類樂器幾乎不見。比如在早期印度、尼泊爾印度教神廟和印度尼西亞的普蘭巴南神廟(建于約公元10世紀(jì))的一些浮雕壁畫里,就只能見到號角和桶鼓兩種樂器(見圖1—圖3):
圖1 南印度印度教寺院樂舞石雕[2]
圖2 尼泊爾印度教寺院樂舞木雕、石雕(楊民康攝)
圖3 印度尼西亞普蘭巴南神廟的吹打樂器石雕(楊民康攝)
關(guān)于其當(dāng)代延續(xù)的狀況,比如在筆者近十年來訪問過的上述一類場所中,位于“印度化”潮流傳播起點(diǎn)和絲綢之路末端的印度、斯里蘭卡等國的印度教和佛教寺院里,每日舉行的祭拜儀式都簡化為由一支嗩吶和一兩只桶鼓構(gòu)成的吹打樂隊擔(dān)任伴奏或用以渲染儀式環(huán)境。到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印度教寺院里,日常祭祀活動中的用樂情況亦如是(見圖4、圖5)。
圖4 南印度印度教神廟的吹打樂隊圖(楊民康攝)
圖5 新加坡印度教神廟里的吹打樂隊(楊民康攝)
(二)較為晚生的佛教音樂和寺院器樂及其與神樂的繼承關(guān)系
在南亞地區(qū),印度教信仰不僅產(chǎn)生、形成的歷史比佛教要早得多,并且佛教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在印度教的肌體上衍化而成。佛教在印度產(chǎn)生之后,曾經(jīng)經(jīng)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發(fā)展演變過程,最終退出了印度本土,而轉(zhuǎn)移到南亞和東亞、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生存發(fā)展。在佛教向外傳播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兩個分支是在早期的上座部佛教(又稱原始佛教或小乘佛教)和大眾部佛教(又稱大乘佛教)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前者由印度渡海遷往錫蘭(今斯里蘭卡)再傳至東南亞中南半島和中國云南,成為今天所稱的南傳上座部佛教或巴利語系佛教;后者則向亞洲其他國家發(fā)展,并經(jīng)中國北方地區(qū)傳入,其后又傳至日本、韓國和越南,成為今天所稱的北傳佛教,又可再分為漢傳佛教(或漢語系佛教)和藏傳佛教。若從佛教音樂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從早期的佛教外傳開始,大乘佛教就比小乘佛教更為重視在佛教儀式過程中使用音樂作為傳播工具和供養(yǎng)手段,并且同時在北傳、南傳以及陸路、海路等不同傳播路徑中體現(xiàn)出來。其中,由于斯里蘭卡和東南亞更為接近印度本土,致使南傳一路比北傳一路的佛教(音樂)傳播更為直接和保持原樣。但或許是缺乏史料記載的原因,以往此方面情況一直較少為人所知。但是近年來發(fā)掘出來的位于這一區(qū)域的吳哥窟、婆羅浮屠等諸多石窟壁畫里,包含了不少可以對之佐證的圖像資料。比如,在已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印尼日惹地區(qū)婆羅浮屠塔寺,于四層方壇回廊上,分布著兩千多幅石雕壁畫,其中描繪了大量的音樂和舞蹈表演場面,分別涉及與俗樂和神樂相關(guān)的兩類儀式或生活場景:一類是用于表現(xiàn)已經(jīng)記載在佛教本生經(jīng)故事中的,佛祖釋迦牟尼入道成佛之前歷次轉(zhuǎn)世過程中的種種塵世生活和講經(jīng)修身的事跡;另一類呈現(xiàn)了當(dāng)時的佛教法會和相關(guān)社會生活中的各種拜佛和祭祀場景。在這兩類圖像場景中,菩薩無論是處在生前或生后的狀態(tài),都幾無例外地占據(jù)中心位置(C位),從事音樂表演的樂工和民眾都簇?fù)碛谄渖舷伦笥腋鱾€方向。不同之處是,生前展現(xiàn)的是菩薩早期在宮中或室外的日常生活及后來講經(jīng)修身的狀況,樂工和民眾所從事的相關(guān)音樂活動即屬俗樂或佛事供養(yǎng)音樂;其生后(成佛)的狀態(tài)則通常由一幅佛龕和佛像呈現(xiàn)出來,周圍的樂工和信眾所從事的相關(guān)音樂活動涉及以吹打樂隊為主的祭祀音樂。其儀式用樂明顯繼承了早期婆羅門教(即后來的印度教)的神樂表演傳統(tǒng)。拙文《印尼爪哇島婆羅浮屠塔寺的樂舞石雕圖像研究》[3]曾經(jīng)結(jié)合許多相關(guān)的樂舞石雕壁畫的例子,對該類現(xiàn)象做過初步的研究和分析,下面將選取其中幾幅有代表性的圖像,再增加更多近年來所獲得的相關(guān)田野考察實例,對本文所關(guān)注的器樂分類問題做進(jìn)一步的討論和解釋。
根據(jù)筆者所獲的相關(guān)田野考察資料,南亞、東南亞地區(qū)與佛教相關(guān)的古代石窟壁畫里,存在較多在法會儀式活動里采用吹打樂隊的情況。與周邊的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同類儀式音樂相比,這類用樂習(xí)慣或與早期印度教神樂的用樂傳統(tǒng)保持了較多的繼承關(guān)系。比如,在下列一幅婆羅浮屠塔寺的菩薩祭祀圖里,佛龕居中,四周為佛教信眾組織的祭祀活動場景。從其中祭祀樂隊采用的七只鼓、三支角、三支豎笛和一具銅磬的樂器組合看,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吹打樂隊(見圖6)。數(shù)量較多、聲量巨大的號角和桶鼓,在其中占據(jù)了明顯的位置。
圖6 婆羅浮屠塔寺的菩薩祭祀圖(楊民康攝)
在其他地區(qū)的佛教壁畫里,只有西藏古格王朝壁畫(約公元16世紀(jì))中吹奏多只長號(筒欽)的場面可以與之相比。當(dāng)然,后者顯示的主要是傳統(tǒng)佛教節(jié)日慶典中的公眾儀式及民俗表演場面,而在藏傳佛教法會儀式里,長號作為儀式法器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與這類圖像中顯示的較純粹的信仰和儀式氛圍比較吻合。但是由于后者在當(dāng)?shù)厥弑诋嬂锍霈F(xiàn)的時間比較晚,并且在現(xiàn)場還配合出現(xiàn)了漢族傳統(tǒng)舞蹈竹馬、舞獅和嗩吶與打擊樂(鼓、鑼)組成的吹打樂隊的畫面,就給予我們對該類節(jié)慶表演是否包含藏漢音樂文化交流元素留下了猜測的空間(見圖7)。
圖7 古格王國遺址紅殿東壁南側(cè)下層慶典圖像(約公元16世紀(jì)上半葉)[4]
關(guān)于石窟壁畫中的樂伎,如今數(shù)量最多、最有說服力和較具有比較意義的,當(dāng)數(shù)迄今所發(fā)掘的中國中原石窟寺群圖像資料。根據(jù)相關(guān)研究,其中較具代表的敦煌石窟壁畫中的音樂圖像可分樂伎和樂器兩類。樂伎又再分為伎樂天(含天宮樂伎、飛天樂伎、化生樂伎、護(hù)法神樂伎、經(jīng)變畫樂伎)和伎樂人(含故事畫樂伎、供養(yǎng)人樂伎、出行圖樂伎、嫁娶圖樂伎、宴飲圖樂伎)。[5]可以說,事關(guān)佛陀生前的日常生活及講經(jīng)修身的俗樂或佛事供養(yǎng)音樂,幾乎遍布其中的大多數(shù)伎樂類型里,但是呈現(xiàn)佛陀成佛之后的供養(yǎng)樂隊場面相對較少,涉及禮佛樂隊的就更為稀見了。并且,其中與禮佛樂隊相關(guān)的場面,多系散布的樂伎微型圖像(比如云岡石窟西壁龕周圍的樂伎群像),所用樂器多屬絲竹細(xì)樂樂種。
(三)當(dāng)代南亞、東南亞佛教寺院法會儀式中的樂器、樂隊及用樂狀況
在斯里蘭卡丹布拉佛教石窟(見圖8)第五窟門外的走廊一側(cè),筆者還碰到了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為游客演奏儀仗音樂的迎賓樂隊。樂隊由嗩吶手和鼓手各一人組成。該類樂隊采用短管嗩吶與直桶鼓(三只一套子母鼓)組合,于每日固定時刻為游客演奏迎賓曲(見圖9)。
圖8 丹布拉佛教石窟壁畫(楊民康攝)
圖9 石窟禮儀樂隊(楊民康攝)
而在斯里蘭卡康堤達(dá)拉達(dá)馬利戛瓦佛教寺院,到了每日早、中、晚3次的日祭時間,在震懾人心的鼓樂聲中(見圖10),由3位高僧分持3把不同的門匙開啟鼓殿大門,進(jìn)入并主持舉行隆重的敬拜儀式,儀式之后再開啟內(nèi)殿拱門,讓信徒與游人從門外魚貫瞻仰供奉佛牙的佛牙塔。
圖10 斯里蘭卡佛牙寺禮儀樂隊(楊民康攝)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jù)相關(guān)史料、考古圖像資料和田野考察資料,在古今北方絲綢之路沿線的北傳、藏傳佛教法會活動(見圖11、圖12)及中國古代北方少數(shù)民族音樂里,采用吹打樂隊(如嗩吶、號角)或笙管樂隊的情況都并非鮮見。而在今天的東南亞與云南南傳佛教寺院的法會儀式里,除了會用象腳鼓樂隊或铓鑼類打擊樂器渲染儀式氣氛外,基本未見采用吹管樂器和打擊樂組成的吹打樂隊。這有助于我們對古代南傳和北傳兩派佛教音樂的特點(diǎn)及其傳播做出兩點(diǎn)猜測:其一,在佛教法會里采用吹打樂的情況自古就有,并且主要存在于大乘(或北傳)佛教傳播區(qū)域;其二,從距離南亞最近的印尼婆羅浮屠塔寺早期即已經(jīng)存在此類現(xiàn)象的情況看,在佛教法會儀式中采用吹打樂器和樂隊的歷史狀況并非是在佛教沿北方絲綢之路傳播過程中才發(fā)生,而是早在佛教自印度和斯里蘭卡產(chǎn)生初期即已經(jīng)存在,并且是分別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和北方絲綢之路兩條途徑,同時向東南亞和云南地區(qū)以及中國北方和境外地區(qū)傳播,并由此形成了與北傳(漢傳和藏傳)佛教和南傳(上座部)佛教相應(yīng)的兩個佛教音樂文化分支。
圖11 四川覺囊藏傳佛教寺院吹打樂隊(楊民康攝)
圖12 不丹藏傳佛教寺院吹打樂隊(楊民康攝)
圖13 不丹佛教寺院打擊樂器(楊民康攝)
二、宮廷雅樂、民間俗樂和地方“土樂”的長期并存和持續(xù)發(fā)展
若結(jié)合佛教(音樂)文化在部分南亞及東南亞地區(qū)的繁盛和“土俗系”樂舞,以及樂器(或器樂)至今仍然保持的情況看,“神、佛、雅(神)、俗、土”四類樂種并存的狀態(tài),在古代南亞和東南亞地區(qū)曾經(jīng)一度形成,并且保持了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其中的“雅(神)、俗、土”三者,又經(jīng)歷了相對獨(dú)立且互相影響、融合、歸并的過程。
(一)“云南-東南亞”宮廷雅樂、民間俗樂和地方“土樂”的分化和發(fā)展
與神樂和佛樂的逐漸消失和偏之一隅相比,俗樂類型中宮廷器樂和民間器樂表演的形象,不僅完好地保留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印尼婆羅浮屠塔寺和吳哥窟的壁畫上面,并且經(jīng)由古代南亞和東南亞宮廷和民間音樂活動的實踐保存,至今能在包括非遺傳承和節(jié)慶儀式、跨國旅游等充滿文化建構(gòu)意味的文化表演場合中見到。比如,在印尼婆羅浮屠塔寺的一幅石窟壁畫“宮廷帝王宴樂圖”(見圖14)里,展現(xiàn)的是佛祖釋迦牟尼生前作為喬達(dá)摩王子的日常生活故事。畫面中間是盤腿而坐的王子,身旁四位侍從里,其右側(cè)(圖像左邊)是兩位猴面奴仆。兩側(cè)的大型宴樂畫面里,皆分為上下兩組。圖像左側(cè)上方一組站立的八人里,前方五人各以不同的體態(tài)、手法,演奏不同形制的絳繩桶鼓。其中一人敲擊兩具直立地上的絳繩大鼓,另外四人皆身挎中型直桶鼓或圓形腰鼓,共計六只桶鼓,后面三人做舞蹈狀。下組九人中,三人分別持(疑似)棍狀匏琴、琵琶和笛子演奏,后方三人似為歌唱演員,另兩人手持盛滿食物、供品的托盤,呈獻(xiàn)給中間的君王。圖像右側(cè)也分上下兩組,上一組站立八人,其前方出現(xiàn)了三位持桶鼓演奏者,其中一人腳踩祥云,呈飛天舞蹈狀;后面的五人各手舞足蹈,或做出深情歌詠的姿態(tài)。下一組坐著的八人中,左數(shù)第四、第五人正面或反身彈奏某種弦樂器,第七人的模樣似在吹笛,但未見樂器,也許已被歲月磨蝕而不見其蹤,其他五人似在歌唱或演奏,由于畫面損毀,已經(jīng)難以一一辨明了。在所有樂舞壁畫中,可以說這是涉及樂器和音樂表演類型最為豐富多樣的一幅圖像。
圖14 印尼婆羅浮屠塔寺石窟壁畫宮廷帝王宴樂圖(楊民康攝)
時至今日,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qū),由于以古代婆羅門教(即后來的印度教)為代表的宗教神權(quán)的逐漸失勢和宮廷階層的退隱和離位,古代的神(雅)樂和俗樂在今天大致可歸并為俗樂,泛指現(xiàn)今主要存在于東南亞內(nèi)圈各國的細(xì)樂和粗樂樂種及其各種樂器(在日本學(xué)者林謙三的“印度系、土俗系”分類中屬于前者)。但是由于這些音樂至今仍然在許多官方和上層社會禮儀中得到使用,并且顯示出其國族文化認(rèn)同的象征意義,所以從深隱文化層面上看,神(雅)樂和俗樂的分類并沒有完全失去其原有的社會功能和實際用途。但是由于這一部分音樂內(nèi)容的占比較小,并且隨著當(dāng)今城鄉(xiāng)社會及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別和距離日漸顯微,導(dǎo)致神(雅)樂、俗樂和細(xì)樂、粗樂的社會功能作用也融為一體,因而總體上可以將之大致歸并于俗樂之中。至于古代東南亞的“土俗系”本土樂器,由于長期的融合與調(diào)適,如今已同樣基本融化到了城鄉(xiāng)一體、階層模糊的俗樂系統(tǒng)之內(nèi)。
在上述廣大區(qū)域內(nèi),自古以來粗樂與細(xì)樂在表演場合上大體是以民間社會和宮廷上層區(qū)分。但是,粗樂樂隊所依存的民間表演場合,除了一般的民間節(jié)慶儀式慶典及其他民俗活動場合外,還一直在印度教、佛教等帶有民間色彩的傳統(tǒng)宗教祭祀里使用,這是前述早期南亞和東南亞神樂產(chǎn)生的基礎(chǔ)。關(guān)于古代的情況,可參見在東南亞內(nèi)外圈交接地帶柬埔寨的吳哥窟,分別以小吳哥寺和巴揚(yáng)寺為代表,體現(xiàn)了印度教和大乘佛教的建筑和佛教文化特點(diǎn),其石窟壁畫也分別采用了以粗樂或吹打樂為主的“行樂”樂隊(見圖15),以及以絲竹樂隊(細(xì)樂,由琵琶、笛、箜篌等樂器組成)(見圖16)為舞蹈、歌唱伴奏。小吳哥寺的石雕壁畫,描繪了許多古代印度史詩所記載的民間節(jié)慶儀式活動及戰(zhàn)爭中的樂舞表演場面,其中龐大的吹打樂隊由直笛、小鈸、匏琴、抬鑼、編鑼、多支號角和各種挎鼓組成,這類樂隊除了在民間儀式里出現(xiàn)外,也常常作為行進(jìn)隊列中的鼓吹樂出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在民間慶典儀式里采用吹打樂隊或打擊樂隊的習(xí)俗,如今在信仰印度教和南傳佛教的民族和地區(qū)也得到了較好的延續(xù)和繼承(見圖17-19)。
圖15 小吳哥寺石雕壁畫里的民間節(jié)慶儀式活動及行樂樂隊(楊民康攝)
圖16 吳哥窟巴揚(yáng)寺壁畫上的宮廷筵宴及細(xì)樂表演(楊民康攝)
圖17 尼泊爾寺院的成年禮儀式樂舞(楊民康攝)
在中國古代情況有所不同。根據(jù)漢文史籍,早期的雅樂也曾經(jīng)主要是宗廟祭祀用樂,后來曾經(jīng)分化出宮廷禮樂和燕樂。東南亞各國過去雖然也有同樣的發(fā)展趨向,但似乎由于缺少文字典籍的原因,如今尚未發(fā)現(xiàn)在其官方系統(tǒng)中有這樣較細(xì)致的分類。只是從唐代的《驃國樂》和明代的《百夷傳》等漢文史籍里,能夠看出漢族文人的某些帶有“他者”痕跡的劃分思維。在印尼的婆羅浮屠大塔寺和柬埔寨吳哥窟的石窟壁畫里,也同樣能夠看到與此類似的真實場景。而至后世,在日本學(xué)者林謙三的學(xué)術(shù)分類里,又將《驃國樂》的幾十種樂器再分為“印度系、土俗系”。其中的“土俗系”,便包括了后來在清代漢文史籍里,亦曾對當(dāng)時進(jìn)貢于清代朝廷的樂舞用“粗緬甸樂、細(xì)緬甸樂”予以劃分。若從當(dāng)時這些樂舞在緬甸應(yīng)用的情況看,其中的細(xì)樂和粗樂,其實也仍然保持和沿用了古代南亞、東南亞地區(qū)較普遍存在的神(雅)樂和俗樂的區(qū)分和應(yīng)用狀況。
(二)區(qū)域性符號:以細(xì)樂和粗樂區(qū)分的民族器樂樂系層疊現(xiàn)象
關(guān)于雅樂和俗樂,乃是筆者所做的學(xué)術(shù)分類,對此有必要提到細(xì)樂和粗樂兩大樂系的區(qū)分。從歷史發(fā)展過程來看,其中的細(xì)樂以彈撥、吹奏樂器和鈴缽為主,最為完整地出現(xiàn)在早期印度到東南亞內(nèi)外圈(馬六甲海峽兩岸)交接地區(qū),在有關(guān)唐代《驃國樂》的漢文古籍和印尼婆羅浮屠大塔寺、柬埔寨吳哥窟中可見記載;粗樂以嗩吶和鼓、鑼、鈸三大件打擊樂為標(biāo)配,以清代漢文史料中記載的緬甸的“細(xì)緬甸樂、粗緬甸樂”分類中的后者較為完善。如今,細(xì)樂和粗樂的完整形式,仍然存在于東南亞內(nèi)圈的一些國家,但在南亞和東南亞外圈的海島國家和中國云南這兩端則不算完整。
在明代李思聰、錢古訓(xùn)撰《百夷傳》中,大百夷樂、緬樂和車?yán)飿罚际呛腕垩缰蟮摹疤蒙稀敝畼罚J笙和村甸大鼓,則是“堂下”之樂,兩者已經(jīng)存在階層化區(qū)分。但是,這僅只是從一個局部的南北文化交匯之地看到的文化縮影,尚不足以概括云南與東南亞器樂文化分布的全貌。若從地域上擴(kuò)展開來看,當(dāng)時應(yīng)該已經(jīng)存在南傳佛教文化圈內(nèi)傳統(tǒng)中心城市地區(qū)的古典細(xì)樂與邊陲村鎮(zhèn)地區(qū)的粗樂——打擊樂之分,前者以緬樂為主,后者以車?yán)飿窞橹鳌2⑶遥谇耙活惖貐^(qū)也會存在著像德宏地區(qū)那樣兩者分層疊立的現(xiàn)象,而在后一類地區(qū)也會出現(xiàn)細(xì)樂文化向下滲透的情況。前者如在緬甸及泰國北部的民間表演中,嗩吶與象腳鼓樂隊結(jié)合形成吹打樂的例子,后者則可見于云南孟連縣宣撫司樂隊的例子。
三、當(dāng)代云南與東南亞樂器與器樂區(qū)域性特征的維系和變遷
再說今天部分南亞及東南亞地區(qū)俗樂與佛樂的關(guān)系,由于在一度以古代婆羅門教(印度教)為代表的傳統(tǒng)信仰和神權(quán)統(tǒng)治,已經(jīng)為今天以“民間佛教”著稱的南傳(小乘)佛教所取代,以經(jīng)文唱誦為主的佛樂系統(tǒng),已經(jīng)具備了與俗樂并立和抗衡的條件和能力,因而形成了以傳統(tǒng)佛樂和俗樂在這一區(qū)域內(nèi)兩者并存和彼此分立的狀態(tài)。
總之,今天能夠體現(xiàn)云南與東南亞區(qū)域性特點(diǎn)的代表性器樂,可分佛樂和俗樂兩類。其中,南傳佛教音樂節(jié)慶儀式音樂是佛樂的主要內(nèi)容。若僅從佛樂的樂器分類看,在早晚課誦儀式(核心層)和法會儀式(中介層)里,所用的樂器和器樂其實非常簡單,主要是體鳴樂器中的大铓鑼、銅磬一類法器。到了節(jié)慶儀式法會(中介層次)里,會加入寺院大鼓舞、象腳鼓樂隊等,用以烘托氣氛。在節(jié)慶儀式歌舞展演活動(外圍層次)里,則納入了象腳鼓樂隊作為伴奏和獨(dú)奏。但即便如此,至今仍然以印度早期樂器分類法中的基本分類和主要樂器為基本范圍。
若從器樂文化的階層性和區(qū)域性特點(diǎn)看,與傳播性較強(qiáng)、市民文化特征較明顯的大百夷樂和緬樂相比,車?yán)飿泛痛蠊臉贩謩e為中國境內(nèi)的西雙版納和德宏本土樂種,傳播能力偏弱。直至600年后的今天,大百夷樂和緬樂已經(jīng)成為東南亞頗具代表性的“細(xì)樂”種類,被應(yīng)用于社會宮廷上層的儀式、筵宴場合;而車?yán)飿泛痛蠊臉穬深悩贩N同樣已經(jīng)互相融合并成為“粗樂”(吹打樂或打擊樂),但仍然僅主要在云南的德宏、西雙版納、普洱等地和緬、泰、老諸國的鄉(xiāng)村地區(qū)流存,并應(yīng)用于各種地方性祭祀、節(jié)慶活動,成為一個與城市音樂“細(xì)樂”相對的次區(qū)域代表性樂種。
從區(qū)域文化角度及“由內(nèi)向外”的視角看,云南與東南亞地區(qū)自前現(xiàn)代時期即形成了云南與東南亞內(nèi)圈以細(xì)樂和粗樂(含吹打樂、打擊樂)的分層并置和外圈以銅樂為主,兼有吹打樂和細(xì)樂的基本分布特點(diǎn)。其中,云南與東南亞內(nèi)圈的結(jié)合部,由外向內(nèi)呈現(xiàn)出吹打樂(圖18、圖19)向打擊樂過渡,而以“車?yán)飿贰焙退略捍蠊臉窞榛緲?gòu)成的特點(diǎn),是較值得關(guān)注的一個重要現(xiàn)象。
圖18 緬甸新蒲甘區(qū)的鼓樂儀仗隊伍(楊民康攝)
圖19 泰國清邁佛教節(jié)慶儀式活動中的儀仗吹打樂隊(楊民康攝)
結(jié) ?語
根據(jù)上述比較的情況看,在古代南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交融,以及印度文化和中華文化兩大文明文化圈的互播和互鑒語境下,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文化經(jīng)由南亞向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傳播,一度形成了某種“印度化”的區(qū)域文化發(fā)展和傳播潮流,并且圍繞中國這個最為重要的傳播中轉(zhuǎn)站和文化集散地,形成了北傳和南傳兩個重要的文化支脈或傳播流派。其中的北傳支脈(北傳佛教為主)主要通過陸路由中國北方進(jìn)入中原地區(qū),再至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南傳支脈(南傳佛教為主)經(jīng)由海路斯里蘭卡,再通過海路和陸路進(jìn)入東南亞和中國云南。在此過程中,相關(guān)傳統(tǒng)音(器)樂也同樣形成了北傳與南傳兩路文化特征和傳播軌跡。其中,北傳支脈有著體量較大、內(nèi)容較多、史料較全的顯著優(yōu)勢,但是也由于距離較遠(yuǎn)、路途環(huán)繞、涉及的民族和文化眾多等外在原因,致使其所傳播的音樂文化內(nèi)容和形式上產(chǎn)生了較為復(fù)雜、多樣的涵化和變異狀況;相比之下,南傳支脈盡管存在著體量較小、內(nèi)容較少、現(xiàn)存史料較為薄弱等特點(diǎn),但由于地域毗鄰、路途相通、民族文化較接近等原因,致使這一支脈里,更多是通過古代石窟壁畫和當(dāng)代樂舞表演實踐,較為完整、原樣地保留了該類傳統(tǒng)文化的原型樣貌和文化特色。
注釋:
[1][印度]婆羅多著,尹錫南譯:《舞論》(上),巴蜀書社,2021,第40頁。
[2]本文除圖7外,其余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3]楊民康:《印尼爪哇島婆羅浮屠塔寺的樂舞石雕圖像研究》,載《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18年第3期。
[4]轉(zhuǎn)引自孺子莘主編:《中國石窟寺樂舞藝術(shù)》,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第572-573頁,圖795。
[5]參見鄭汝中、霍旭初:《中國石窟寺音樂圖像概論》,載孺子莘主編:《中國石窟寺樂舞藝術(shù)》,人民音樂出版社,2009,第7頁。
往期回顧(向上滑動閱覽)
絲綢之路音樂研究從《樂家錄》看絲綢之路東線的“船樂”(上)
從《樂家錄》看絲綢之路東線的“船樂”(下)
絲路,西部音樂文化“覓母”的喚醒與“新西域想象”
絲綢之路上的音樂及其傳來樂器研究日本藩校的“樂”實踐——以弘前藩校稽古館為例從《體源鈔》看中國典籍與日本樂書的關(guān)系
一帶流動的音樂風(fēng)景 —隋唐西域音樂與中國性的體現(xiàn)
城市與音樂:中古時期發(fā)生在洛陽的樂工流動遷移與聚合
多媒體交響劇場《絲路追夢》的創(chuàng)作特色和文化內(nèi)涵探析
關(guān)于中亞的絲路音樂研究:概論篇絲綢之路上的橫笛及其東漸
敦煌曲子、變文與貴池儺戲中的《孟姜女》
古代日本送葬儀式的藝能文化 ——亞洲大陸文化的導(dǎo)入及發(fā)展
關(guān)于中亞的絲路音樂研究:相關(guān)成果篇
豈知重得兮入長安——中古樂工圍繞長安的流動遷移與聚合地理文化證
絲綢之路上的復(fù)合簧管樂器研究(上)——雙簧樂器的東漸與西漸
關(guān)于中亞的絲路音樂研究:基礎(chǔ)資料篇(上)
關(guān)于中亞的絲路音樂研究:基礎(chǔ)資料篇(下)
南亞戲劇在跨喜馬拉雅貿(mào)易線路上的傳播(上)
以中古為對象,看加強(qiáng)城市與音樂研究的重要意義(下)
中亞音樂的范疇、屬性及其音樂、藝術(shù)和文化特征(上)
浙江音樂戲曲研究《浙江戲曲音樂》序言浙江近現(xiàn)代音樂社團(tuán) ?“春蜂樂會”中堅人物沈秉廉研究浙江山歌曲調(diào)的源流關(guān)系與發(fā)展脈絡(luò)(上)浙江山歌曲調(diào)的源流關(guān)系與發(fā)展脈絡(luò)(下)
宋代音樂研究論北宋雅樂樂論的撰述類型與撰述語境南宋音樂文化的歷史繼承性和地域性《宋代樂論》導(dǎo)論、《宋代樂論》輯錄:論音樂的生活南宋臨安市民音樂文化的形成機(jī)制研究《宋代樂論》輯錄:論禮樂體制
《宋代樂論》輯錄:論音樂展演
宋代演藝市場的市場結(jié)構(gòu)及營銷策略探析 —音樂史與經(jīng)濟(jì)史的跨學(xué)科探索
宋代古琴音樂文化整體歷史發(fā)展思考 ——編年史體例與宋代古琴音樂文化研究
民族音樂研究跨界族群音樂與世界民族音樂研究的親緣關(guān)系——兼涉云南與周邊南傳佛教音樂文化圈的幾點(diǎn)思考主體借鑒與客體乞靈——對民族音樂現(xiàn)狀的文化理論思考地戲重建與身份認(rèn)同——西南黔中長順營盤鄉(xiāng)民屯堡文化傳承個案傳統(tǒng)曲體在近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運(yùn)用——以板腔體對中國歌劇創(chuàng)作的影響為例
牛津西方音樂史研究塔魯斯金歷史文述中的捷克音樂家——兼談其對民族樂派的態(tài)度20世紀(jì)音樂之“斷” —塔魯斯金《牛津西方音樂史》第Ⅳ卷與第Ⅴ卷問題劃分、框架及思路
從塔魯斯金的《牛津西方音樂史》看音樂史的撰寫視角、觀念與方法
理查德·塔魯斯金《牛津西方音樂史》中世紀(jì)部分閱讀札記二則
曾志忞史料世紀(jì)之問(一) ——曾志忞史料“殆近”之歟?世紀(jì)之問(二) ——曾志忞史料“殆近”之歟?
世紀(jì)之問(三) ——曾志忞史料“殆近”之歟?
世紀(jì)之問(四) ——曾志忞史料“殆近”之歟?
浙江音樂與戲曲研究《浙江戲曲音樂》綜述(上)《浙江戲曲音樂》綜述(下)
浙江漢族民歌音樂形態(tài)初探 (上)
浙江漢族民歌音樂形態(tài)初探 (下)
書評豐富·邏輯·趣味 ——讀林華《音樂審美心理學(xué)教程》
當(dāng)代歌劇藝術(shù)發(fā)展的理論之境 ——居其宏《歌劇美學(xué)論綱》的時代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叢書》序國內(nèi)西方音樂體裁研究的開創(chuàng)之作——錢亦平與王丹丹《西方音樂體裁及形式的演進(jìn)》讀后
音樂歷史與創(chuàng)作分析
促進(jìn)傳統(tǒng)樂理向作曲實踐的轉(zhuǎn)化管色十二律位系統(tǒng)的旋宮實踐與音律結(jié)構(gòu)—系列研究之一:“陰陽旋宮”的音律結(jié)構(gòu)與律制模型流浪者”構(gòu)建的理想國度 ?——析舒伯特《“流浪者”幻想曲》的創(chuàng)作特色
對中國歌劇創(chuàng)作幾個問題的看法
豈知重得兮入長安——中古樂工圍繞長安的流動遷移與聚合地理文化證
音樂家“生命史”的歷史表述上海工部局公共樂隊創(chuàng)建初期的五位指揮(上)
上海工部局公共樂隊創(chuàng)建初期的五位指揮(下)
壯族麻江型銅鼓的音色屬性及協(xié)和度分析研究
音樂學(xué),請把目光投向音樂!
從樂舞圖像看笙的西傳
淪陷時期哈爾濱放送音樂活動研究
世界音樂與文化
T.C.Fabrizio,J.Farrington等|文本資料與田野考察手冊(一)
T.C.Fabrizio,J.Farrington等|文本資料與田野考察手冊(二)
[美]蒂莫西·賴斯 著,魏琳琳 譯|民族音樂學(xué)理論(上)
[美]蒂莫西·賴斯 著,魏琳琳 譯|民族音樂學(xué)理論(下)
音樂絲綢之路研究
關(guān)于中亞的絲路音樂研究:基礎(chǔ)資料篇(上)
關(guān)于中亞的絲路音樂研究:基礎(chǔ)資料篇(下)
[孟加拉]賽義德|南亞戲劇在跨喜馬拉雅貿(mào)易線路上的傳播(上)
[孟加拉]賽義德|南亞戲劇在跨喜馬拉雅貿(mào)易線路上的傳播(下)
音樂歷史與創(chuàng)作分析
壯族麻江型銅鼓的音色屬性及協(xié)和度分析研究
音樂學(xué),請把目光投向音樂!
從樂舞圖像看笙的西傳
淪陷時期哈爾濱放送音樂活動研究(上)
以中古為對象,看加強(qiáng)城市與音樂研究的重要意義(下)
音樂絲綢之路研究
以中古為對象,看加強(qiáng)城市與音樂研究的重要意義(上)
以中古為對象,看加強(qiáng)城市與音樂研究的重要意義(下)
中亞音樂的范疇、屬性及其音樂、藝術(shù)和文化特征(上)
中亞音樂的范疇、屬性及其音樂、藝術(shù)和文化特征(下)
歌劇理論與實踐探討
音響詩學(xué)——瓦格納樂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 樂譜筆記并相關(guān)問題討論(1)
音響詩學(xué)——瓦格納樂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 樂譜筆記并相關(guān)問題討論(2)
音響詩學(xué)——瓦格納樂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 樂譜筆記并相關(guān)問題討論(3)
音響詩學(xué)——瓦格納樂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 樂譜筆記并相關(guān)問題討論(4)
浙江戲曲與音樂研究
音樂歷史研究
徘徊在嘉陵江上(1)
音樂歷史與創(chuàng)作分析
論史學(xué)結(jié)構(gòu)的邏輯性和史學(xué)觀念的隔閡現(xiàn)象
巾幗一揮手 ?如聽萬壑松——趙家珍教授及其古琴藝術(shù)世界
讀書樂評嶺南音樂文化的多學(xué)科闡釋嶺南音樂文化的多學(xué)科闡釋(下)
音樂歷史與創(chuàng)作分析《單刀會》雙調(diào)[新水令]字調(diào)腔格初探——基于語言音樂學(xué)視角的元雜劇旋律風(fēng)格考辨之一(1)《單刀會》雙調(diào)[新水令]字調(diào)腔格初探——基于語言音樂學(xué)視角的元雜劇旋律風(fēng)格考辨之一(2)《單刀會》雙調(diào)[新水令]字調(diào)腔格初探——基于語言音樂學(xué)視角的元雜劇旋律風(fēng)格考辨之一(3)《單刀會》雙調(diào)[新水令]字調(diào)腔格初探——基于語言音樂學(xué)視角的元雜劇旋律風(fēng)格考辨之一(4)
音樂歷史研究
音樂作品分析
奏鳴曲式的音樂進(jìn)程及其潛在的結(jié)構(gòu)——杜鳴心《小提琴協(xié)奏曲》第一樂章之曲式解
杰克·波蒂“管弦樂音色織體”結(jié)構(gòu)與“迻譯作曲”研究(上)
杰克·波蒂“管弦樂音色織體”結(jié)構(gòu)與“迻譯作曲”研究(下)
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專欄
音樂美學(xué)研究
之于音樂學(xué)范疇與音樂史進(jìn)程中的三個學(xué)科問題(上)
之于音樂學(xué)范疇與音樂史進(jìn)程中的三個學(xué)科問題(下)
易簡工夫終久大 新知培養(yǎng)轉(zhuǎn)深沉——試論漢語語境中的音樂美學(xué)與音樂史學(xué)的學(xué)科分野與交融
“感性認(rèn)識”之路——國內(nèi)音樂美學(xué)學(xué)科“感性認(rèn)識”相關(guān)問題闡發(fā)
音樂文化傳播與交流
音樂歷史研究
音樂與文化研究
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專欄
主體性作為精神自由的呈現(xiàn):貝多芬的“突現(xiàn)”主題
創(chuàng)作與表演分析
《幻想波羅涅茲舞曲》的創(chuàng)作草稿:調(diào)性問題(上)
《幻想波羅涅茲舞曲》的創(chuàng)作草稿:調(diào)性問題(下)
譜外之“譜”的聲音秩序:琉球民謠合奏“交互”即興表演民族志(上)
譜外之“譜”的聲音秩序:琉球民謠合奏“交互”即興表演民族志(下)
“勞弗特藏”專欄
“音樂學(xué),該把目光投向何處”
無論目光投向何處,都要踐行科學(xué)研究原則音樂學(xué)研究的重點(diǎn)是音樂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雙重格局與本體內(nèi)核——兼論建立“中國傳統(tǒng)音樂理論體系”的意義
湘昆研究請把目光投向創(chuàng)承人——基于湘昆口述史視角的探索
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兼談黃翔鵬先生的學(xué)術(shù)特點(diǎn)
“音樂”·“文化”·“人”:民族音樂學(xué)研究的三個層次
“越劇改革80年”專欄
口頭創(chuàng)腔與活口演唱:越劇演員的創(chuàng)腔和演唱傳統(tǒng)
一份珍貴的越劇音樂文獻(xiàn)——讀《浙江省越劇團(tuán)音樂研究小組業(yè)務(wù)總結(jié)報告》
藝術(shù)感受是強(qiáng)烈的、深遠(yuǎn)的——以越劇《祥林嫂》為例談越劇音樂改革
以史為鑒 繼往開來:從浙江小百花越劇團(tuán)首次晉京演出戲單談起音樂絲綢之路研究從敦煌壁畫中的彎琴形象看鳳首箜篌的文化內(nèi)涵絲綢之路上的印度琵琶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東地區(qū)中外音樂文化交流
榆林窟第25窟無量壽經(jīng)變圖“音聲之相”研究中亞音樂研究(二)——樂器的分類、制造及其圖像學(xué)研究中緬傣撣族群佛寺大鼓配置及其音聲釋義
一件在歷史上被忽視的東方樂器——絲綢之路上的水平式角型豎琴研究絲綢之路上彈撥類樂器的東漸與流變
敦煌壁畫中所見鼗鼓與雞婁鼓兼奏圖論考
從《五弦譜》至《三五要錄》中的兩首同名曲看中國唐樂在日本的變遷(上)從《五弦譜》至《三五要錄》中的兩首同名曲看中國唐樂在日本的變遷(下)從《樂苑》的文獻(xiàn)來源再看唐代的孤柱現(xiàn)象樂舞在敦煌壁畫中的空間與表現(xiàn)中國音樂史與博物館參與式教學(xué)探析——以絲綢之路上的音樂物質(zhì)遺存為例論“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東方音樂文化認(rèn)同
琴意誰可聽?(上)——?dú)W陽修之琴與北宋士風(fēng)
琴意誰可聽?(下)——?dú)W陽修之琴與北宋士風(fēng)
音樂歷史研究
編鐘、編磬文物的試奏——以海昏侯劉賀墓編鈕鐘和澄城劉家洼M1鐘磬為例
衰微中的繁榮——易縣燕下都遺址編磬研究
論曾侯乙甬鐘“正聲”加“新鐘”樂律關(guān)系的省略變化與論述特點(diǎn)
復(fù)古與變通:清中葉禮樂詮釋的兩種路向——以汪烜、江永為中心
古代琴論經(jīng)典文本的分析與研究——張岱琴學(xué)“生鮮之氣”理論的現(xiàn)代闡釋
獨(dú)托幽巖:簫友梅戰(zhàn)時辦學(xué)的處境、思想與心境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昆腔研究(三)
論京房六十律的推演模式和歷史價值新賓滿族傳統(tǒng)婚俗音樂文化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客家“跳覡”音聲文本的互文性建構(gòu)與符號學(xué)解讀
民族音樂學(xué)
《苗蠻圖》傳世音樂畫本演繹內(nèi)容與歌舞分類研究西北空間視域下的秦腔北傳考論
創(chuàng)作與表演研究
中國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思維方式和特征探賾文獻(xiàn)學(xué)視域下的俄羅斯音樂文獻(xiàn)整理與研究——以九所音樂學(xué)院學(xué)刊發(fā)表論文為例(1989-2019)
民間旋律的交織與素材變形帶來的(非)連續(xù)性(上)——解讀陳怡《八板》(1999)民間旋律的交織與素材變形帶來的(非)連續(xù)性(下)——解讀陳怡《八板》(1999)
中國當(dāng)代流行戲歌創(chuàng)作研究——以京歌為例
鋼琴獨(dú)奏曲《望海》解析
用音樂言說——馬勒《第二交響曲》的敘事布局與結(jié)構(gòu)寓意直接轉(zhuǎn)調(diào)與變音轉(zhuǎn)調(diào)——中國揚(yáng)琴樂器改革的兩種思路中國新生代作曲家室內(nèi)歌劇創(chuàng)作的比較與思考——以《娜拉》和中央音樂學(xué)院“歌劇計劃”若干作品為例“宋韻”在二胡作品中的創(chuàng)作與演繹15世紀(jì)Suavitudinem Redolent理念之作曲實踐研究——基于弗蘭基諾·加福里奧《音樂實踐》的解析
宋代音樂文化研究蔡元定音樂著述新論房庶《補(bǔ)亡樂書》輯考文本中的聲音景觀——再思南宋都城臨安的音樂文化研究北宋樂論中的雅俗之辨蘇軾詞調(diào)音樂的藝術(shù)革新——以樂器為中心的考察
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謝紹英:被遺忘的留美音樂先驅(qū)抗戰(zhàn)勝利初期《松花江》重唱末刊手稿研究“同均三宮”理論在應(yīng)用當(dāng)中的幾個問題論先秦兩漢文獻(xiàn)關(guān)于琴作為禮器在周禮中的使用
青年學(xué)術(shù)論壇國劇運(yùn)動的歌劇理想與實踐——國立戲劇專科學(xué)校樂劇科成立始末試探清末民初浙東地方戲赴滬發(fā)展之因古琴凄涼調(diào)調(diào)意研究關(guān)于永嘉雜劇歷史分期問題之考辨千呼萬喚始出來,未成曲調(diào)先有情——“催妝樂”初探
音樂絲綢之路研究美索不達(dá)米亞的箜篌鉤沉柏孜克里克第48窟銅鈸圖像稽考
“施光南音樂藝術(shù)專題學(xué)術(shù)研討會”專欄(一)青春飛揚(yáng) 個性剛強(qiáng)——中央音樂學(xué)院附中階段(1957-1959)的施光南一首歌曲的作用施光南聲樂作品中民間音樂素材的應(yīng)用與藝術(shù)形象塑造
“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學(xué)術(shù)研討會”專欄(一)音樂的區(qū)域性、民族性、現(xiàn)代性與歷時性——論吳越傳統(tǒng)的“長三角”音樂與文化關(guān)系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的學(xué)理反思與學(xué)術(shù)建構(gòu)
論江南音樂文化轉(zhuǎn)型的三個視點(diǎn)
傳統(tǒng)音樂研究中華文化多元一體視野下臺灣梵唄的形成與發(fā)展孤殘安頓:盲人說唱表演中的社會倫理“勞弗特藏”中國早期錄音中的民間歌曲分析與歸類
音樂創(chuàng)作與分析“和而不同”視域下的文本生成方式——朱踐耳民樂五重奏《和》研究昌英中弦樂四重奏《旋文》音高材料探究音樂之翼:民族樂隊的融合之美——郭元民族管弦樂《蝴蝶扇動翅膀Ⅱ》配器技法分析
青年學(xué)術(shù)論壇音樂心理劇治療因素研究援書論琴:論書學(xué)理論向琴學(xué)理論的滲透
音樂絲綢之路研究論絲綢之路上的變文、講經(jīng)文音樂(上)勝金口7號佛寺伎樂童子圖像抱持樂器考辨
傳統(tǒng)音樂研究在對話中認(rèn)識自我:關(guān)于中國傳統(tǒng)音樂當(dāng)代傳承與傳播的思考
“施光南音樂藝術(shù)專題學(xué)術(shù)研討會”專欄(二)在旋律如歌性與交響戲劇性之間不懈探索——再論施光南歌劇創(chuàng)作及其當(dāng)代啟示從施光南歌劇《傷逝》到改編版室內(nèi)歌劇《紫藤花》之結(jié)構(gòu)嬗變引領(lǐng)時代風(fēng)潮 把握發(fā)展脈搏——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創(chuàng)作與傳承啟示
“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學(xué)術(shù)研討會”專欄(二)傳統(tǒng)音樂學(xué)科的主體性實踐與審視——江南區(qū)域中的吹打樂種教研敘事大區(qū)域音樂歷史文化研究的展望——為首屆“長三角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論壇”而作論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三部“海派”電影音樂作品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江南都市笛樂演奏家群體研究
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常璩《華陽國志》著錄宗旨與音樂觀念考辨乾隆時期河北地方志民俗音樂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以《中國地方志集成?河北府縣志輯》為例
音樂表演研究二胡早期練習(xí)曲的建構(gòu)歷程河西走廊民歌《月牙照花臺》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及流播問題探析
音樂美學(xué)研究之于音樂學(xué)范疇與音樂史進(jìn)程中的三個學(xué)科問題(上)之于音樂學(xué)范疇與音樂史進(jìn)程中的三個學(xué)科問題(下)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美學(xué)的研究——我的理解、思考與論述路徑(上)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美學(xué)的研究——我的理解、思考與論述路徑(下)
易簡工夫終久大 新知培養(yǎng)轉(zhuǎn)深沉——試論漢語語境中的音樂美學(xué)與音樂史學(xué)的學(xué)科分野與交融
“施光南音樂藝術(shù)專題學(xué)術(shù)研討會”專欄(三)施光南歌劇《傷逝》創(chuàng)作的人文情懷與藝術(shù)追求施光南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民族敘事——基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視角用旋律譜寫時代強(qiáng)音——施光南音樂藝術(shù)館開館暨《施光南全集·聲樂卷》首發(fā)系列學(xué)術(shù)活動綜述
音樂與文化研究絲綢之路上的胡旋舞、胡騰舞論音樂人類學(xué)多元文化理念中的音樂教育功能及其中國實踐
音樂創(chuàng)作與分析歌劇曲式(一)歌劇曲式(二)歌劇曲式(三)歌劇曲式(四)
音樂歷史與文化研究“勞弗蠟筒”的價值及其研究中的問題——兼評《中華民族音樂蠟筒(清末晚期)原聲集成》“以歌舞演故事”——從樂舞與百戲的結(jié)合再溯戲曲之源夏威夷尤克里里在20世紀(jì)中國的興衰史客家“下壩迎燈”儀式音樂的符號隱喻與文化認(rèn)同
創(chuàng)作與表演分析《幻想波羅涅茲舞曲》的創(chuàng)作草稿:調(diào)性問題(上)《幻想波羅涅茲舞曲》的創(chuàng)作草稿:調(diào)性問題(下)
青年學(xué)術(shù)論壇二里頭文化鈴器三題
抗戰(zhàn)時期高等音樂學(xué)校的建立與發(fā)展——以福建音樂專科學(xué)校為例(1940-1945)
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專欄貝多芬歌劇《菲岱里奧》中的多元世界表現(xiàn)貝多芬接受史中的“男性氣質(zhì)”生成
“勞弗特藏”音樂檔案館研究系列勞弗“蠟筒”中的歷史回聲穿越百年的聆聽——“勞弗特藏”中上海部分戲曲蠟筒錄音的音樂學(xué)研究再探“伯特霍爾德·勞弗檔案”中的《上海胡琴》
音樂絲綢之路研究論絲綢之路上的變文、講經(jīng)文音樂(下)《敦煌樂譜》有、無標(biāo)題曲的旋律關(guān)系研究論“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東方音樂文化認(rèn)同從新疆地區(qū)壁畫看唐代琵琶的孤柱現(xiàn)象
歌劇學(xué)研究新世紀(jì)中國歌劇旋律寫作與主題從復(fù)調(diào)思維看歌劇作品的多層結(jié)構(gòu)——以譚盾《牡丹亭》為例瓦爾特·費(fèi)爾森斯坦:德國歌劇導(dǎo)演的創(chuàng)新與影響
紀(jì)念周大風(fēng)100周年誕辰專題周大風(fēng)“逆向”音樂教育思想探微周大風(fēng)說越劇配音(上)
音樂文化研究江蘇近現(xiàn)代二胡學(xué)派歷史文化特征的多維闡述19世紀(jì)西方關(guān)于中國音樂的理論著述——以阿里嗣與李提摩太夫人的《中國音樂》為例
中國傳統(tǒng)音樂研究昆腔研究(四)中國傳統(tǒng)音樂結(jié)構(gòu)思維在當(dāng)代流行音樂創(chuàng)作中的運(yùn)用站人秧歌的藝術(shù)特色及文化意義——以齊齊哈爾、茂興、塔哈秧歌為例
創(chuàng)作與表演分析譜外之“譜”的聲音秩序:琉球民謠合奏“交互”即興表演民族志(上)譜外之“譜”的聲音秩序:琉球民謠合奏“交互”即興表演民族志(下)
音樂歷史研究《永樂琴書集成》真?zhèn)卧倏?/span>楊蔭瀏晚年佚文《中國音樂發(fā)展概述》輯釋曾侯乙編鐘結(jié)構(gòu)中律位觀念及其今用北宋音樂美學(xué)思想綜論——以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為中心《樂府雜錄》中的音樂批評初探編鐘、編磬文物的試奏——以海昏侯劉賀墓編鈕鐘和澄城劉家洼M1鐘磬為例稿 約
一、本刊為全國性音樂理論學(xué)術(shù)季刊。本刊遵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發(fā)表音樂各領(lǐng)域的研究成果,反映人們在中國傳統(tǒng)音樂與舞蹈、絲路音樂歷史與文化、宋代音樂文化、浙江戲曲音樂、世界音樂與文化以及音樂演繹與創(chuàng)作等問題的討論及關(guān)注。歡迎在上述領(lǐng)域具有較高學(xué)術(shù)性、創(chuàng)新性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來稿。
二、思想活躍、角度獨(dú)特、觀點(diǎn)新穎的稿件優(yōu)先刊用。來稿以中等篇幅為宜,篇幅長者一般不超過15000字。請附200字左右的內(nèi)容提要以及3至5個關(guān)鍵詞(作者能提供文章題目、內(nèi)容提要和關(guān)鍵詞的英文譯稿最佳)。引文、參考文獻(xiàn)必須準(zhǔn)確標(biāo)明出處(如作者、出版者、出版年月、版本頁碼等)。一律用尾注,翻譯稿請附原文和版權(quán)授予書,譜例請用五線譜。
三、來稿請附上作者簡歷,包括真實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所在單位、職稱(或?qū)W位)、職務(wù)、詳細(xì)地址、郵政編碼、電話號碼以及電子郵件信箱。
四、本刊編輯部不辦理退稿,作者請自留底稿。請勿一稿多投。三個月內(nèi)未接本刊對稿件的意見,作者可對稿件自行處理。恕不另奉審稿意見。
五、稿件一經(jīng)刊用,即付稿酬。除作者特別聲明外,文章發(fā)表后,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即授予本刊,不再另付稿酬。
六、本刊編輯部電話0571-89808178。歡迎通過電子郵件信箱與本刊編輯部聯(lián)系和投稿。E-mail:[email protected].
為繁榮我國音樂學(xué)術(shù)研究,推動學(xué)術(shù)發(fā)展,發(fā)據(jù)新生力量,培育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人才梯隊,發(fā)揮刊物的育人功能,本刊擬開設(shè)主要面向在校大學(xué)生的"青年學(xué)術(shù)論壇"專欄,歡迎在讀及畢業(yè)一年之內(nèi)的博士、碩士、學(xué)士積極投稿,特別歡迎有朝氣、有銳氣、有深度的創(chuàng)新之作。稿件具體要求如下:
1、要求文章內(nèi)容為原創(chuàng)性研究成果;
2、要求選題聚焦于某一具體音樂現(xiàn)象、音樂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3、選題不宜過大,篇幅以8000-10000字左右為宜;
4、一般性的研究綜述、書評、田野考察報告等不在本欄目選題之列;
5、來稿可附導(dǎo)師100字左右的簡要點(diǎn)評(博士亦可自評),點(diǎn)評請明確指出論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和學(xué)術(shù)價值,精彩點(diǎn)評發(fā)表時可以一并刊出。
掃描二維碼關(guān)注我們
微信公眾號 | 音樂文化研究
監(jiān)制:孟凡玉
審定:陳沛
審核:王菲菲
編輯:孫銳

![]()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關(guān)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fèi)查看免費(fèi)推送
- 衢州招標(biāo)網(wǎng)
- 杭州招標(biāo)網(wǎng)
- 湖州招標(biāo)網(wǎng)
- 嘉興招標(biāo)網(wǎng)
- 寧波招標(biāo)網(wǎng)
- 紹興招標(biāo)網(wǎng)
- 臺州招標(biāo)網(wǎng)
- 溫州招標(biāo)網(wǎng)
- 麗水招標(biāo)網(wǎng)
- 金華招標(biāo)網(wǎng)
- 舟山招標(biāo)網(wǎng)
- 樅陽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廣州奧天海鵬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 梅州梅縣華僑中學(xué)招標(biāo)網(wǎng)
- 無錫工程造價信息網(wǎng)
- 呼倫貝爾市人民政府
- 河北應(yīng)急廳
- 宿州公共資源交易網(wǎng)招標(biāo)
- 來賓招標(biāo)網(wǎng)
- 棚改招標(biāo)
- 陪標(biāo)出場費(fèi)一般是多少
- 東光縣財政局
- 南京政治學(xué)院
- 西南|采購網(wǎng)招標(biāo)公告
- 高陵區(qū)招標(biāo)
- 明光市工程建設(shè)招標(biāo)網(wǎng)
- 合川市信息網(wǎng)
- 撫順市建設(shè)工程招標(biāo)網(wǎng)
- 攝像機(jī)招標(biāo)
- 南皮縣教育局
- 臨汾招標(biāo)信息網(wǎng)
- 廣東建設(shè)網(wǎng)
- 中國科學(xué)院中關(guān)村醫(yī)院
- 海安政府招標(biāo)網(wǎng)
- 那曲招標(biāo)投標(biāo)公共服務(wù)平臺
- 永修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陜西招標(biāo)與采購網(wǎng)招標(biāo)公告
- 三沙市招投標(biāo)中心
- 招投標(biāo)收費(fèi)管理辦法
-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招標(biāo)信息公示網(wǎng)
- 秦皇島財政招標(biāo)
- 滎經(jīng)縣招投標(biāo)中心
- 寧夏工程建設(shè)招標(biāo)采購公共平臺
- 浙江省招投標(biāo)信息網(wǎng)
- 江蘇思源赫茲互感器有限公司
- 灤州市招投標(biāo)中心
- 保潔招標(biāo)公告
- 南師附中宿遷分校
- 濟(jì)陽縣招標(biāo)
- 北京市東城區(qū)花市小學(xué)
- 河南省政府采購網(wǎng)招標(biāo)投標(biāo)
- 鐵嶺市人民政府
- 陜西省招標(biāo)信息公示網(wǎng)
- 孟津縣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招投標(biāo)知識點(diǎn)和重點(diǎn)
- 云南機(jī)電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
- 天津美術(shù)學(xué)院
- 任丘市政府網(wǎng)
- 第|十三飛行學(xué)院
- 澠池縣人民政府
- 岱山教育網(wǎng)
- 金鄉(xiāng)招標(biāo)采購信息
- 營口招標(biāo)公司
- 廣西科聯(lián)招標(biāo)中心有限公司
- 揭陽招標(biāo)網(wǎng)
- 遼寧政府|采購招標(biāo)中心
- 招標(biāo)采購公司有哪些
- 南陽市高新區(qū)
- 嵩明縣人民政府
-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xué)
- 增城區(qū)財政局
- 電器采購招標(biāo)文件
- 銀行培訓(xùn)招標(biāo)
- 句容市教育局
- 定海區(qū)教育局
- 土購網(wǎng)|信息
- 涼城縣應(yīng)急管理局
- 徐州建筑招標(biāo)
- 采購管理ERP
- 安徽采購與招標(biāo)網(wǎng)
- 遼寧建設(shè)工程信息交易網(wǎng)
- 惠東縣惠東職業(yè)中學(xué)
- 陽谷縣教育局
- 四川政府采購網(wǎng)招標(biāo)采購
- 學(xué)校招標(biāo)文件
- 梅江區(qū)人民政府
- 遼陽招標(biāo)采購網(wǎng)
- 中煤陜西公司招標(biāo)網(wǎng)
- 單縣招標(biāo)網(wǎng)
- 施工總承包招標(biāo)文件
- 昆山招標(biāo)信息
-
 聯(lián)系客服
聯(lián)系客服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信息發(fā)布
信息發(fā)布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招標(biāo)訂閱
招標(biāo)訂閱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商機(jī)挖掘
商機(jī)挖掘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數(shù)據(jù)定制
數(shù)據(jù)定制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標(biāo)書代寫
標(biāo)書代寫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資質(zhì)辦理
資質(zhì)辦理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投標(biāo)咨詢
投標(biāo)咨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證書查詢
證書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
-
 綠色報告查詢
綠色報告查詢
 掃一掃 添加微信
掃一掃 添加微信